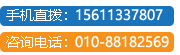

靳之林
3月23日,久画廊推出了“靳之林的绘画艺术之一——故乡之路”展览,靳老先生是一位低调的艺术家,他谦和而又慈祥,年龄虽大,却依然笑声爽朗,语言铿锵有力。展览展出了靳之林多次回到故乡创作的风景油画作品,他的作品多为中国北方农村的风景和田野绘画,展览描述的是他从50年代第一次回到故乡之后至今的绘画。
访问人:袁加 靳军
时间:2011.03.01
地点:北京东城区中央美院宿舍楼
访:靳先生好,听说您刚出差回来。这次去了多久呀?
靳:从河南到山西,前后加在一起有一个多月吧。我整个走一圈,再画了一点,画的不多,因为还有考察的事情。
访:作为油画家,您热衷于考古学及对整个中国文化精神文脉的梳理发展。在这方面您可能是做得最深入的画家了。而在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思考上,您又是如何与自己的绘画经验相对接的呢?
靳:大概是这样,开始的时候是进入到传统文人画。我从高中二年级开始临摹王石谷的画。那时候,校外的老师是吴镜汀,从1946、1947年都是跟他学的。而校内的老师是李智超,李智超就是当时“国画论战”的一方,徐悲鸿先生是另一方。北京的画家比较保守,传统功底比较厚,跟他们主要是学石涛,主要还是临摹,当时我没有创作。有创作的话也是综合传统的画法,画四条屏,山水的春夏秋冬什么的。这是我开始画画的基础,这个很重要。
当时有一个书画研究会,记得是“冬青书画研究会”。学生毕业以后要教小学,所以很重视音、体、劳、美。我们在一个房间,每天上午自习。上完自习时会先在那儿点炷香,让心先静下来,接着才开始临摹王石谷的画。我现在有一幅还留着呢。文革的时候抄家弄烂了,不过当时也没人要这个,要的都是我的印象派画册。1947年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北平艺专。1948年,北平艺专从东总布胡同搬到校尉胡同来,李宗仁给的这块地方,徐悲鸿就写了“德林堂”,就是后来的大礼堂。这个时候的徐先生是提倡新中国画,所以他那时请李可染先生,教我们临摹《八十七神仙图卷》,之后他又陪着齐白石先生给我们上中国画课等。在当时这都是创新,和我高中那时候的教学是不一样的。我有传统绘画的基础,这有好处,假使我没有传统的那一段,一下接触到李可染先生,特别是齐白石这样的大师,我可能就如遇烟云地过去了。也就是因为我有基础,所以当他们在教的时候我很容易就学进去了。齐白石不讲课,他就是表演给我们几个人看……。记得是在艺术“八”教室。因为我是班长,所以我在第一个位置。齐白石就是先从我那儿开始,第一课我记得是画荷花。徐先生先教我们研墨,这个墨要研的出沟来,没沟墨就太稀了。但是有沟它得合上去,要不合上就太稠了,也不行。要一碗水,水多一些,因为齐白石不涮笔。这个是他很特别的地方,但是启发很大。他上来这个毛笔饱饱如提斗,往墨里面一蘸,半个笔尖的前半头都是墨,水淋淋的,上去他就在这画荷花叶,荷花叶画完不涮笔,再一蘸,又是淡的,他先画这边,然后再一蘸,淡了,再画那边。到最后笔上实际上都没有墨了,他还在画。这几下子,几乎就看不出黑白来了,裱上才能看得见,要不裱上都看不到了。然后再画整个荷花杆的穿插,最后点那个墨点。点墨点的时候,李苦禅先生也教过,他说:『墨点下去的时候,这个墨点不是滴下去的,也不是摁下去,他说这个笔滴到这儿了,也就摆到这儿了。那个墨点滴到那儿了,笔也就到了。这样的话,它的气是连接的,光是点儿,在那儿它没气。拿笔甩的那种点儿不行,但是摁的也不行。我感觉这个整体的布局,到最后那个杆儿很重要。
我过去也没有太多地去总结这些,徐先生安排的教学,我感觉受益很深。后来我在中央美院的学术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我也提出过这个建议,油画的专业能不能够加入中国画课呢?我认为,加入此专业并不会影响到油画色彩的提高。相反的,是打开另一个新的视野,对这方面的加强修养还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董希文先生。1956年以后,我是作为助手在董希文先生工作室。董先生工作室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是油画民族化,第二个是民族化基础上的百花齐放。那时,我跟董先生接触比较多。董先生家里案头上摆的一个宋代的梅瓶,白底黑花,磁州窑,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因为他从《开国大典》到《春到西藏》,到《红军不怕远征难》。整个画的过程从始至终我都很熟悉的。包括我到浙江,到光华楼他的老家。董先生睡在哪个床上,我也睡一睡。他在艺术上的素养更让我想了解他的整个生活环境,在董先生老家,遇见到他的堂叔,就问他:董先生小的时候最喜欢什么?他画什么?他告诉我他喜欢玻璃画,那个《三国演义》,拿出玻璃画一看,太漂亮了,我没看过那样的。那是当地的工匠画的玻璃画。因为玻璃画就是勾线的,填色的时候在后面,线的那种流畅感实在太厉害了!
访:董先生的父亲是不是也有很多收藏?
靳:对,也有很多收藏,这其实对他的影响很大。
访:他的家乡是在什么地方?
靳:在绍兴。光华楼,这是个水乡。在1956年,我们两个带着学生到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我画那个《妇女组间棉苗》那个地方。董先生也画过。临走的时候老乡让董先生留一点字画给他们。晚上,董先生拿起毛笔来,画水墨的菊花。我一看,太精彩了。老乡很懂,哪个画得好,哪些地方精彩,比咱们的学生都懂,咱们的学生倒是讲不出来。老乡对笔墨怎么样,精神不精神,都很清楚。它有中国文化在里边……
在董先生家里面,我看《开国大典》的巨画。云彩,鸽子的点法,那些用笔,既有中国画法,又有中国民间艺术的表现力。那种玻璃画的线条,色彩的那种装饰风格。在他的《春到西藏》和《长征》里,他把磁州窑这样的画法,融在他的油画里面,这个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一直是希望尊从徐悲鸿先生、吴作人先生的写实路线走的,不过在那时我也同时受到了现代派的影响,在素描里面我搞立体派,冯法祀先生不但没有阻止我,还支持我。我正是不断的在挖掘自己所找不到东西,古元的木刻、解放区的民歌,陕北的民歌过来,一下子,我就像找到了自己一样。古元的这条道路,原来是我最高的目标,它主要是质朴,这也是我自己的最高美学理念,所以我就希望接下来画完革命博物馆的《大生产运动》,《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然后1961年再接着《南泥湾》,之后就到陕北落户。因为要表达出农民的画,是必须到农民生活中,实地去感受、体会的。
到了延安我那时候就不是画家的想法了。我对延安的感情等于是在一种磨难及更深的情景中成长起来。为了要建设延安,成为“建设者”中的一员。画画是我的一个手段。因为我是画画的,画画怎么能够鼓动,能够为生产服务,为延安的建设服务。所以我要把自己贡献给延安。那个时候完全扑在“农业学大寨”上。
访:从一开始您喜欢徐先生的《吹箫》这种绘画的表达方式,是第一个阶段。到后来您又喜欢古元对社会的这种深切关怀的创作方式,这两个转变是当时知识分子非常普遍的心态。在这个以后,我觉得您在对董先生中国油画、艺术民族化的想法,包括对周围绘画群体的了解和对社会整体认识的基础上,您的艺术在后来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靳:我接着说下来就是这个了。改革开放,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在文化馆工作,那个时候整个的工作重心转移了。因为什么呢?就是光是上层建筑解决不了经济基础的问题,还是达不到建设延安的目的。所以问老乡,什么时候生活最好?回答:“是毛主席在那儿的时候”。那时候耕三余一,耕二余一,吃饱穿暖。现在反而吃不饱了。那么大的力量用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并没有解决延安建设的问题,最后还是转到解决生产方式的问题。因为我跟老百姓比较贴近,所以认识到迫切问题就是文化面临着断裂的问题。这个断裂是人为造成的,是政治因素造成的。那个时候我就想,人还在,搞剪纸的大娘还在,这些民间艺术的群体还在,这个文化就可以恢复。这是我这一生里面可能最重要的一刻,开始呢作为徐悲鸿先生的学生,进入艺术的殿堂。之后古元同志的木刻又让我找到了自己,让我到延安去。但是到了延安以后,感受到民间艺术的质朴、粗放、自由,更广阔的感情天地,这种更加豪放的自由,我喜欢。所以那个时候,发动了一个全区的民间文化普查,目的就想把这个文化传下来。
在这个普查的过程,包括十三个县、市,我直接要参加的有两个县——安塞和洛川。在这个剪纸的普查过程中,我明白了剪纸不是单独的艺术活动,都是跟社会生活连在一起的。比方说,“抓髻娃娃”。以前剪纸里头我也没见到过,从来没见到过,我自己收集的剪纸里头也没有这个。最后还是一个不到六十岁的妇女白凤莲,胆子比较大,她说她剪那个“抓髻娃娃”。一剪出来,我就认出是“抓髻娃娃”。我就问这是干什么的?她说招魂的。娃娃从岸畔上掉下去了。你剪个这个,搭上他的衣服叫上他的名字,在十字路口那一烧,把水倒在那儿,再拿着衣服喊着娃娃的名字回来,这个就是给娃娃招魂。那边呢,又剪了一个“抓髻娃娃”,是坐着莲花盆儿的。我说这个呢?他说这个是“喜娃娃”。“喜娃娃”是干什么用的?她说不是招魂的,是生娃娃的。还有坐着凳子的,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凳子就是催生的“生”,然后查《说文解字》的时候呢,催生的“生”,生娃娃的。然后呢,又剪了一个手拉手的,这个“手拉手”的叫做瓜子娃娃。瓜子娃娃什么意思呢?她说“天不怕、地不怕,单怕瓜子娃娃一把叉”。我说什么叫做一把叉呢?她说就是这么一站,妖魔鬼怪谁也不敢吃了。因为这个东西是五个,也叫“五道娃娃”。我说的不是 “舞蹈娃娃”,叫“五道娃娃”。“五道娃娃”是东西南北中五方神来保护我们家,有招魂的,有辟邪的,用途不一样。我就感觉到这个东西时间很远了,这里面的问题有很多了,这个可能是我思想上最重要的一个转折。后来呢,我闹不清楚,就跑到社会科学院,我的老朋友赵超,他搞古文字学,在考古所。他给我介绍到他的图书馆,帮着我借了很多的书。那时候我有五年的时间基本上是读书,想解决这些问题。最后我搞清楚了,整个的民间艺术就两个内容,:一个是永生,生命的生存;还有一个就是繁衍。除了这两个以外再没有第三个。这两个升华为哲学,就是阴阳相合,化生万物。没有阴,没有阳,不可能有人类,也不可能有动物,也不可能有生物。自然的生物,植物它也要花粉的交配。没有力学作用和反作用就没有物理;没有化合的分解就没有化学;没有正数和负数就没有数学。宇宙也是,宇宙它为什么没有阴,这暗物质一出来,我觉得还得要有阴。总是要天地相合、阴阳相合、男女相合、雌雄相合,这就是一个阴阳相合才能化成万物,这是一个阴阳观。第二个,化成万物以后它不是消亡,而是生生不息。一代一代往前发展,永生不息。
我觉得人类的文化意识可能是两个,就是阴阳相合,化生万物。一个生命意识,一个繁衍意识。上升为哲学,就是阴阳相合,化生万物,万物生生不息。我觉得中国画、中医也是这个。中医讲的就是你病了,是阴虚还是阳虚,阴虚补阴,阳虚补阳,就是《黄帝内经》。所以后来我感觉,石涛并没有说清楚“画论”,但是《黄帝内经》说清楚了。如果美术学院上第一课,是讲《黄帝内经》,那中国画就好办了,就理解了。不光是多少描,十八描,十八描的根是什么东西都明白了,就是整个一直进到他的哲学和美学领域里面去,因为这基础还是哲学。如果是这样的话,看一下书法就知道了,它的阴阳关系了,抑扬顿挫,起承转合,这些就明白了。阴阳相合,化生万物,万物生生不息。其实笔墨也好,书法也好,就好比中国画,上边是天,下面是地,所以叫做山水人在其中,天地人的关系。然后空白,这地方不能漏气,漏气不行,这种观念不是西方的这个数学观念了,不是黄金分割律了。上来就得一笔上去,然后根据气的运行来组织构图。这我就想起齐白石的画荷花表演,它是从气连接上来的,整体的。从这一点来看,集中在中国人的哲学思想里,也就更好理解了,一下子就容易抓住了本质的东西。《黄帝内经》是作为人和万物关系的哲学理念,它用到社会的话,我想就应该是儒家。所以我就认为孔子是个伦理学家,不是哲学家。哲学还得问老子。因为伦理学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这个儒家的核心是什么?是在社会上搞的那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君的君,当臣的为臣,我觉得这个都很适合,子是有子的道,夫有夫的道。这是一个整体的和谐社会,所以中国的文化、社会两千年没有断裂,应该归功于儒家。但是儒家的思想又归功于中国的本源哲学,那是一个民族的根。这种想法建立了以后,我自己拿起笔再画画时,就开始感觉融进去力量了。从1978年到1988年再到1998年,这几十年时间的思考,最后我总结出:“仰观宇宙之大,俯瞰万物之胜,万物与我合一,万物与我生生不息”。万物就是我,我就是万物,根上还是从本源哲学来论述的。
现在呢,我的危机感就在这里。这个哲学是通过符号来表达的,不通过符号怎么表达哲学?很难。就是没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文化符号。原来的符号那么多,现在呢,结婚只剩下一个,就是喜字。然后过年就剩下一个,就是“福”字,福到。吉祥符号就是一个,中国结。实际上中国结最早七八千年前就有中国结。后来呢,我到希腊去,它的墓碑上头就有中国结。非洲那个面具上头中间就是中国结。然后到了红山文化六千年的玉猪龙玉器,中间也是中国结。中国结最多的地方,罗马的米开朗基罗,他的《最后的审判》所在的西斯廷。西斯廷的地板上全是中国结,是各种不同的变体,我觉得最丰富的还是在西斯廷那儿。然后呢,最早我看到中国结的图片是在土耳其,那八千年前就出来了,那个比中国还早。中国最早的河姆渡,河姆渡是七千年,后来到大汶口出来的中国结,六千年。后来到了陕西半坡,“渔网”符号,那个“渔网”符号就是中国结,两个,这个符号到处都在用,两个菱形,或者是加三个菱形。这个我是有意地考察的,全国各个省,从南到北,从新疆到青岛,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全是。三个菱形,两个菱形。画的时候呢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觉得都是中国结的变体。生生不息,这个都没有了的话,它这个载体就没了,它都是通过文化符号来传达的,这个符号包括国画。
我不同意“笔墨等于零”。笔墨的符号、书法的符号,都是通过这个,这个都没有了,那你这个文化载体,哲学载体,本源哲学的载体就没了。原来这个根儿是一个总根儿,一个大树的根儿,就是本源哲学。后来,分裂了,分裂为各家治学。儒家、道家、诸子百家出来了。后来到汉代的儒学,宋代的理学,然后再发展,再往下发展就是现代的和谐社会。如果这个根儿没有了,这些也就没了。所以,我感觉这个对我的画的影响是什么呢?我原来还是比较关注具体的地方的,或者是一个人的气质,比如说陕北,这个地方很质朴,黄土高原的质朴、人的质朴,这是一种精神。还有一个呢,是生活,比如南泥湾,毛主席大生产运动,关注的还是现实主义。现在呢,我感觉升华了,关注的不只是一个具体的事物。而是关注一种道了,一种观念了。
访:那您现在是不是在油画绘画上,这种用笔的表现跟这个思想也有关系?
靳:对了,我说的就是这个。在构图上,我就是根据气来了。我上来就画我这个感受。我还是重视生活感受,但是着眼点不是在这儿了。而是将这种生活感受,有一种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的意思。
访:它就不在具体表现那个的东西现象了。
靳:对,不在具体的东西,而在于道了,都是在论道。这个道就是生活感受,已经成为如果没有这个道,我可能就动不了心。有这个道呢,一下子就有很强烈的一种情感和感受。这都是从生活感受来,并不是从观念抽象那里边来,从观念抽象里边来说话,我想就是在搞史论了。而作为艺术家、画家来说,这种理念是转化为情感了,这个情感包括他对生活的观察,包括他对情感的表达,所以我很喜欢“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句话。不是在表现这个事情上,画这个人也不是表现这个人,画这个景也不是表现景,而在于山水之间,山水之间那就是万物与我合一,万物与我统一。
访:您说的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是关于中、西艺术的基本出发点的差异。比如说中国人是一个生活化的观念艺术,实际上是用艺术来解读生活方式。在根本上呢,它是要表达这样一个思想过程,一种随生活而动的观念艺术。但是西方的艺术呢,它相对来讲比较重视客观性。但我感觉老一代艺术家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他们非常重视写生这个概念,从生活里直接获取形象,或者是色彩,或者表现现实空间关系这样一种意图。您是怎么样考虑在现实和主观之间,取得平衡?因为我也知道,您是特别喜欢写生的一个画家。
靳:对。
访:您那么大岁数了还要每年都到各地去写生,直接面对真实的生活客观世界,同时呢,您又是一个非常中国式思维的艺术家。这种现象在以往很多中国艺术家的身上都有所反映,只不过没有您那么强烈。比如说过去很多油画家,如徐悲鸿先生,吴作人先生,或者刘海粟先生,他们的早期的油画,西方式的绘画,和他们后来的中国绘画相比,尽管不能说没有联系,但是我们看到其间很远的距离,就是差别。但这个东西在您身上有一种特殊性,就是说您在主观意识上已经强化地要把它们揉在一起的这个概念。就是既从西方艺术包括色彩、空间的塑造的这种方式,您都在画面里极力地在保持。但是,又要把中国的这个所谓的道、气,这种对于世界的看法,对生命的理解,要灌入到您现在的绘画里去,您在这个方面是怎样一包括笔意、笔触的角度,或者从构图的角度,来谈一谈您是怎样构想的。包括对现在的艺术教育,也给我们谈一谈。
靳:好,这个题目面比较广。这么些年,我也一直在理这个头绪。一个是西方传统的油画,我比较重视它的色彩。传统的油画,我为什么非要写生不可?因为,比方说我的画,如果一万张画应该是一万张调子,不能够有一千张调子,不可能重复。这个不重复的原因呢,就在大自然,它给你的条件色是不同的,每一种条件色给你的一种调子,色彩的调子是不能重复的。给你感情的每一种影响,每一种感受,都是不同的。这个是从我学画开始,跟徐先生学画的时候,我就一直是拿这个作为色彩表达的最高要求。因为这个就是表达自己的情感。整体的色调有具体的明暗、前后、空间、色彩间的转化所共同来组成的。但是最后呢,它也组合成一个,就是董希文先生讲的色彩表情。他每一张作品,都有他所追求的一个色彩表情。像画肖像,很多细微的表情,如果没有观察到的话,那种感觉,那人的个性很难表达。这个我觉得这是油画的灵魂,是靠我直接的感受得来的。我并不是把这个色彩关系画对了,我就满意,不是。这个色彩感受,包括很多因素,对这个地方的了解,历史文化的了解、地域、环境、风土人情、人的个性,它是一个统一的了解。这样的话,我觉得是自己精神上的一种满足。另外,关于绘画的表达方式,就拿毕加索来说吧,中国人看不懂毕加索,为什么呢?他那个符号不是中国的符号,中国的文化基因不是那个样。它像那个半导体带导波段式的,他没感应。你的这个基因里边没有那个,所以不能说中国人素质低,素质低为什么他看懂董希文先生为农民画的那个,一下子他就给你评论了呢?你写书法,我有的时候在农村给他们留字的时候,人家一看哪一篇好,哪一篇不好,一下就出来了,哪一笔好,哪一笔不好,也都很清楚。但是咱们的美术学院的大学生不一定能够像农民眼睛那么清楚。但是他们可能看毕加索他们了解,而中国农民看毕加索不行。因为那个符号不是中国的文化基因所产生的符号。所以我觉得,中国艺术是形而上的,它那是形而下的,这种观念离不开它一种所谓科学性的抽象,无论康定斯基也好,毕加索、柏拉图也好,马蒂斯也好,波堤切利,这些呢,我觉得它还是形而下的,不是形而上的。我觉得最关键的应该是一种哲学观念。哲学观念所产生的美学观念,它的艺术观念,哲学体系决定它的艺术体系,艺术体系决定它的造型体系和色彩体系。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我想中国艺术往前发展的时候会用中国的哲学形而上,来进到中国的抽象。中国也不是说完全都是用写实所能够代表中国,或者是抽象所代表中国,它不存在抽象或具象的问题,它不是一种形而下基础上的抽象或具象。我问董先生,我说什么叫中国艺术、中国画?,他说就是写意。我说那工笔呢?写意是写意,工笔也是写意。一写意呢,就是形而上,就是中国哲学的那个。另外一个呢,也不是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这种概念了。像齐白石是现实主义的还是非现实主义的?不是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呢,还是西方的。抽象和写实也是西方概念。中国不存在这个。这样一种观念的转变,我想应该是中国自己本土艺术的一个发展,一个趋势。
访:其实现在呢,倒是我们大部分美术学院的学生,对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表现方式,失去兴趣和判断力,没有感觉了,这是艺术教育的失败。他们对西方从古典到现代,甚至到后现代主义的关注度很高,还有解释它们的可能。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整个的主线,失去解读能力了,这是很可怕的,这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断代的现象。
靳:这个我想到原来的中国画家,都是文人。他要琴棋书画都要行的。刚才我说的符号的考察,实际上是棋,不了解棋,也不了解中国的本源文化。然后琴也好,不懂得这个音不行。所以“礼、乐、射、御、书、数”,乐就占第二了。你一定要成为秀才,你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不懂乐不行,而乐呢,是民族文化群体的,从几百年前就是这个旋律,极其重要。然后呢,他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诗是民歌,你得懂得民歌,民间的诗,要懂得民间的音乐,这些,都要懂得。所以,我觉得三十年代的老一辈还是这样的,我的老师这一辈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文化人。中国的画家,石涛、八大他们,首先是文化人。如果这一点断裂的话,我想中国文化,包括中国的绘画,就会断裂的。这个是不能断裂的。
访:您刚才说的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个叙述,能够了解您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的基本思路,这个对今天的中国艺术家是特别有意义的。您平常如何安排时间画画的呢?
靳:我这一年里大概就是这样,这么多年以来也一直还是这样。春天的时候,画那个迎春花。在北京那么多年了,跑到中山公园,后边的红墙,古老的中国焕发青春。这个是新中国以后,是我这一代人,一直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古老的中国焕发青春。所以先画迎春,画完迎春,玉兰开了,我就赶紧到颐和园,每天都要画玉兰。玉兰蓝天和白的,很圣洁的这种白的玉兰在一起,这是中国文人画的东西,原来田世光先生教我们工笔重彩的时候,看宋徽宗的,也是蓝底白玉兰,那种感觉很圣洁,这个时候画的感觉又不一样了。这种东西可能还都是文人画的情怀、感觉,追求的是人格的高尚,或者人格的美。而这个人格的美呢,是由中国本源哲学的生命意识和繁衍意识所派生出来的。画完了以后呢,藤萝开了,赶紧的,离玉兰比较近,转过来就是藤萝。画藤萝最过瘾了,画枝条用皴擦,怎么画都可以。藤萝完了画牡丹,牡丹原来我很喜欢吴先生画的牡丹,用笔的转折。吴作人先生画的是静物。我觉得西方的油画呢,把这些活的花都作为静物了,而且把活着的动物,螃蟹、兔子,把兔子吊在那儿,这个都是把有生命的东西变成没生命的东西了。为什么他要这么画?因为他要表达它的质感,表达它的亮感、空间感,画得跟真的一样,这个它必须摆在那儿。画鱼,他如果不画死鱼,他没办法表达那个鱼的亮感、质感、空间感。一画活的,这个就不行了,你还没画完它跑了。所以,它叫做静物。中国不是,中国不是在花瓶里的,不是把东西弄死,而画的都是活的,所以它叫做花鸟。
上回我在中央美院展览里,就是花鸟山水的油画展,只画活的,不画死的,这就是一种观念的变化。所以,我画的野鸭子在河塘里头游,画兔儿吃白菜,兔子是活的,不是吊起来的,中国就不会画那个的。因为中国是生命意识,它的生生不息是个主导的哲学观点。山水也是,它不是画一个景,而是画天、地、人的关系,画天地合一。上边有山,空闲,下边有水,然后人在其中,这样一种关系呢,是人和宇宙的融合。西方是画具体的一种景色。中国画就是道,漏气不漏气也是在道的那个范围里边。所以,用在山水静物画展上,我想关于静物画也好,风景画也好,会是这种中国哲学理念上发展。画人呢,我想可能不光是一个笔墨的问题。我画完牡丹之后,画山药。山药是杆儿比较长,花头往下来,画的时候,它的朝气蓬勃的那种感觉更强烈,比牡丹还要强烈。画完了以后,就该画荷花了。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我还是用《爱莲说》的观点来画荷。表现整体生生不息的一种张力,一种感觉。画完荷花之后,接着我又跑回老家画玉米,这个时候天气开始是最热的时候,荷花也是最热的时候。先从玉米地开始,再到玉米地的收获,到玉米地的垛,之后也就完成了玉米地的整个收成。接下来,我就跑去了陕北。一直画到下雪的时候,大雪来了,我就开始画黄河、画雪,画苍苍茫茫的景致,也是其中有毛主席《沁园春》那种意境。画窑洞里的雪,黄河的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画黄河,大河九曲十八弯,天地合一。然后中间一个烟儿出来了,烟儿一出来,我感觉灵魂飞上天了,然后我就说,那我埋在这儿了。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我就埋在这儿了,下边看黄河。过年就在那儿了。
访:太有意思了。我觉得您的这个绘画方式非常具有中国艺术家的特殊的情怀。一直是跟着天地在走,这个概念很大、很有意思。您从考古学里体会的这些经验,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这种理解,形成了您的绘画气质和面貌。您的实践、探索和努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我们今天的中国是特别重要的。谢谢您。
• 中国角型毛巾架行业运营态势与投资潜力研究报告(2018-2023)
• 中国直接挡轴市场深度研究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2021-2023)
• 2018-2023年KTV专用触摸屏市场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
• 中国回流式高细度粉碎机市场深度调研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3)
• 2018-2023年中国原色瓦楞纸行业市场深度研究及发展策略预测报告
• 中国雪白深效精华液市场深度调研及战略研究报告(2018-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