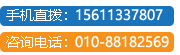
晚上七点半,夜幕刚刚降临。
一帮穿着紫红色衣服的妇女正在一座体育场内欢快地扭秧歌。
如果在下午六点,这个体育场内更是活力盎然:足球场上好几支小球队各自占领着一块地盘厮杀,其余的则在外围观战,或在一旁自顾自地颠球。体育场北侧墙外,双向车道都在堵车;东侧墙外绿化带的台阶上坐着一对紧紧依偎的情侣,离他们不远处,两个小贩儿分别叫卖着“蟑螂药”、“手机贴膜”……好一副生动、平常的世俗生活图景。
这里是泰达体育场。
27年前,这里还只是离天津市区50公里的一片盐碱滩。1984年12月2日,当这里拉进第一车土时,改变天津未来城市格局的基因被激活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TEDA-Tianjin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音译“泰达”)在此动工。
但在1984年至今的大多数时间里,泰达只是由一条条宽阔平整的马路、一栋栋现代化厂房构成的工业园区。下班后,这里一片沉寂。不过,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最终将这个定位为工业园区的地方推上驶往城市化之路的快车:2009年,天津开发区与周边行政区合并,成为新行政区滨海新区的下属区之一,迈出了向综合性新城发展的关键一步。
向城市转型的开发区不止泰达一家。
最近几年,广州、大连、北京、武汉、杭州的开发区相继打出“新城”概念。早在1992年就与所在行政区合并的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在其“十二五”规划中表示,要“由郊区型向城区型转变”。从最初纯粹为地方招商引资的产业园区,逐渐转向集产业与生活为一体的新型城市,它们在功能上开始融入城市发展的主流和主体,成为城市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并走出了一条“开发区-工业化-城市化”成长路径。
这种转变并不仅仅是几个开发区自身转型的故事——鉴于数量众多的开发区在所处城市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甚至可以说,它们决定了未来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
而这更意味着中国从此开始了从政治之城时代向经济之城时代的嬗变:自古以来,中国都是由政治权力配置要素资源、进而塑造城市——凭这一点,汉唐时期的都城长安、宋时的临安、元明清三朝的北京,均曾成为所在时代世界城市中的翘楚;而如今,政治之手一手圈定的一个个“以工业为主”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却不可阻挡地将自己推向城市演进之路。
虽然,这只不过是印证了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经济发展只有常规没有奇迹”的规律,但于一个古老的大国而言,转变之路从来都不轻松。
1. “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
什么是开发区?它仅仅是一块地,上面有很好的设施和密集的企业,并实行一些优惠政策吗?
“是,也不尽然。”沈奎说。
沈奎1986年即参加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现任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研究室主任。
他最推崇的是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对开发区的定义:开发区是为远渡重洋来到的一种新的文明提供的一个停泊的港湾,一个登陆的码头,是为一种新的文明的种子提供发芽的苗床,为新的文明的幼苗、植株提供生根、定植、壮大的园圃;为新的文明、新的生命的那个‘蛋’,提供孵化的舒适、温暖的‘窝’,让它能破壳而出,茁壮成长。
“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开发区的内涵最深刻的诠释。它将开发区与新的文明联系起来,道出了开发区最根本的意义。开发区的诞生,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创新之举。”沈奎说。
1980年代初的中国,尽管建基于“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的对外开放政策已经确定、经济特区也已蹒跚起步,但对“要不要办”特区的认识尚不统一。1984年1月4日至2月17日,邓小平考察深圳、珠海、厦门3个经济特区,回京后即提出“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施特区的某些政策”。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沿海部分港口城市座谈会,确定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
“每个城市设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起步,面积都不大。”国务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
也是在这次沿海城市座谈会上,当时在天津工作的李岚清提出:开发区不仅是创造一个吸引外资、加速经济发展的“小环境”,而且要强调引进先进技术,建议叫“经济技术开发区”。该建议得到支持并被会议所采纳,“经济技术开发区”由此得名。
以此次座谈会为起点,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宁波、广州、湛江、天津、连云港、南通、福州、上海12个城市先后建起了首批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2. 经济“孤岛”
对于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确定了“以工业为主、以外资为主、以出口为主”的“三为主”方针。
首批经济技术开发区面积都不大,大多在10平方公里以下,最大的天津开发区亦不过30平方公里,且还是一小片一小片的滚动开发,比起后来动辄规划面积上百平方公里的开发区,简直小的可怜。
与面积小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早期的开发区大多选址在远离主城区的地方:除上海当时没有选择浦东,而是在市区边缘搞开发区;“神州第一开发区”大连开发区选在了离市区30公里的金州湾……
选址决定了开发区一出生就成为了“地理孤岛”,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各自干各自的,交流被隔离。这深刻地影响了日后开发区的发展走向。
亲历开发区发展历程的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副巡视员王恺在其《走出孤岛》一书中透露,我国提出通过沿海14个城市的扩大开放以实现在特区基础上“接力式”发展的希望时,“在当时遇到了各种阻力,尤其是观念上的阻力是很大的,并非每个人都能接受,包括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
因此,中央要求开发区的选址有一条前提,就是离开母城区,选择空间上易于隔离、便于封闭的地方”,“显然是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一种异己力量,担心外资企业影响、干扰我们的经济体制”。
“那时甚至有人提出,要用围墙将开发区围起来。”中国开发区协会副秘书长周振邦对当年的情形记忆犹新。
国务院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曾走访众多开发区。他发现, “早期设立开发区时,最大的困难是资金,到远离城市的不毛之地开发建设,成本比较低。”
伴随着开发区的高速增长,开发区“孤岛效应”愈加明显。
按照王恺的观察分析,因为开发区经济发展动力系统单一依靠外资企业,使得开发区成为“经济孤岛”;因为在国家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功能定位单一,使得开发区成为“功能孤岛”;优惠政策只能在开发区内有效而不能外溢,使得开发区成为“政策孤岛”;而受到种种“孤岛”效应的影响,开发区建设者形成的“心理孤岛”更成为开发区开放发展思维的大敌。
如此一来,随着开发区的发展,其困局越发凸显。王恺认为,困局的实质不在于孤岛上产业发展环境的不理想,甚至单就硬环境而言要比母城区优越得多,但“企业不得不考虑社会综合环境的差异”。
2004年底,因为“青(青岛市区)黄(黄岛开发区)不接”所带来的交通问题,曾爆出澳柯玛集团总部机关将迁离青岛开发区的新闻。
“走出孤岛”成为开发区发展的必然选择。《走出孤岛》甫一出版,就在开发区系统内引起广泛讨论和认同。
3. 走出“孤岛”
开发区迅速发展的另一个结果是,开发区内、区外形成巨大落差。这使地方政府对开发区有了更多期待:让开发区来示范、带动周边发展。
周振邦将开发区的这一处境形象地比喻为“双肩挑”:中央批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赋予了其国家的使命;地方政府划一块地给开发区,希望用开发区来示范、带动周边发展。
辐射带动周边发展最直接的后果是,开发区规模扩大、企业增多,区内工作人员对生活配套环境的需求增加。此时,“还把开发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作场所,员工在开发区与母城之间‘钟摆式’奔波的工作与生活模式已不合时宜。”沈奎说,“虽然开发区经济上获得成功,但城市不能只发展经济,需要区域协调平衡,不能‘一边是欧洲一边是非洲’——开发区以前就是在围墙里只管自己的,现在就要求开发区带动周边发展。”
沈奎1986年刚到广州开发区的时候,规划的开发区只有9.6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两三万;到1990年代末,已经开发到30多平方公里,后来加上广州科学城,一共60多平方公里,人口有二三十万人了。“人的聚集就形成了社会,就需要向城市转变,而城市是一个系统、多要素组合。”
开发区城市化呼之欲出。
此时,开发区自身的问题也逐步暴露。
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将中国开发区的发展归纳为“卫星平台式”发展——“外资只是为了利用当地便宜的土地、劳动力,形势一变,外资就可能转移,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性有疑问。”
此外,作为中国加速工业化的产物,早期的开发区除上海虹桥外,绝大部分均属于工业园区型,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在70%以上,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开发区生存和发展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给首批14个国家级开发区的财政优惠政策已经到期。
从1999年开始与国家实行完全的分税制;国家利用外资的政策调整和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国家级开发区已有的发展模式受到新的挑战。
产业环境方面,国家提出了“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新要求,国家级开发区面临提高产业关联度,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产业聚集”的问题。以改善综合投资环境为新起点,开发区在扩大利用外资上面临更多的竞争。
社会环境方面,随开发区的日益成长壮大,遇到以往单纯工业区的定位与综合城市化发展需要的矛盾。为了进一步支持工业发展,金融、商贸、社区、文化、教育等功能有待完善。
“开发区不能只考虑生产链的一段,而应考虑完整的生产链;不应仅仅是加工制造业,而应考虑整个产业配套。”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总顾问陈青洲说,开发区城市化已不容回避。
2004年开发区成立20周年时,吴仪代表中央对开发区提出,要向多功能综合性产业区转变。
“上述要求隐含着开发区城市化的意思。”周振邦这样解读。
开发区实际发展过程中,“随着开发区产业集聚、功能完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市场的形成、人才的集聚,城市功能就开始逐步显现:开发区里不仅有工作,还要有生活,于是,城市功能开始形成。”周振邦说。
4. 通向城市之路
大多开发区选择同行政区合并,走出了“开发区+行政区”的城市化之路。
被认为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具有开发区性质的深圳蛇口工业区,在2004年全国调整开发区的大环境中,被列入397个需撤销的开发园区之列,成为现在深圳市下属的行政区南山区的一部分,蛇口管理局建制随之撤销。
2003年,广州开发区托管了一个镇、几个村。2005年以广州开发区为基础成立了一个新行政区——萝岗区。开发区和行政区合并,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开发区体制不变,并占主导,负责经济开发,行政区负责社会管理。
“这是顺应社会需要,自然而然的调整过程。”沈奎说。
无独有偶。之前的2002年底,宁波开发区与北仑区合并,实际上完成了自己的城市化之路。
与此同时,像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合肥开发区、哈尔滨开发区等全国一大批开发区,无论是出于区内产业发展、与所在行政区的协调发展等原因,都开始迫切面临改革现行管理体制的局面。在“走出孤岛”的共识下,更大规模的开发区城市化将成为必然趋势。
“虽然开发区的口号——‘三为主’——还没变,但各个开发区的取向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实际上都在向新城区的方向走。”肖金成说。
通过开发区和行政区合并,开发区实际管辖的范围已经不是当初设立核准的几平方、十几平方公里的范围,而是扩展到几百平方公里的区域。天津开发区300平方公里,广州开发区390平方公里,大连、青岛开发区都是400平方公里。
几百平方公里的大开发区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纯工业园区,而是按照统筹二、三产业、统筹城乡建设、统筹区域发展的理念进行建设的复合开发区或综合经济区。
“开发区成为城市新区已是不争的事实,并且代表着城市最现代的一面。”周振邦说。但他认为,“开发区在城市化中的贡献才刚刚开始”。
这是过去“规划”——“早期根本就没有规划,就是领导在指点江山,工作人员在地图上画圈”——开发区时所不曾料到的:“那时认为开发区就是搞工业的,并没有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这么清晰的思路”。在开发区早期的建设中,生活设施也是作为投资环境的配套,而不提‘城市化’——“那时技术落后,根本不敢提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而走到今天,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发区人已可以在开发区的‘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开发区在城市化中的作用了。”周振邦说。
5. “合并是体制创新”
对于开发区与行政区合并,起初国家开发区的主管部门、更高层级的主管领导并不赞同。广州开发区的一位前任领导曾披露,2005年,广州开发区并入新成立的萝岗区时,有关部门屡次警告,甚至以取消国家级开发区头衔相“威胁”,但最终,还是没能扭住势头。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总顾问陈青洲介绍,主管部门对开发区和行政区合并持否定态度是担心,“给开发区的特殊优惠政策是给特殊区域的,如果行政区都用这个政策,财政无法承受。”
陈青洲自己倒是很理解合并行为:第一,经济技术开发区处于所在城市开发开放的前沿,带动、推动着所在城市的改造,因此,城市将经济技术开发区包容进去也是应该的:早期很多开发区远离市中心,生活基础设施薄弱,合并成行政区、建设新的生活设施,惠及员工、惠及家属、惠及民生,带动了开发区环境的改善,无可厚非。第二,开发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国家使命,在合并后并没有丢,而是仍在做。
“如果地方是用自己的资金、国家使命又没丢,应该鼓励。”陈青洲说,“现在中央没有政策,开发区行政区合并都是地方自己在做。”
周振邦认为,开发区城市化之路大多选择与行政区合并,“是开发区管理体制不明确的结果”。
“开发区刚起步时,主要功能是吸引外资,兴办现代工业,是希望在原有体制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因而把很多的社会事务抛给了地方,是‘轻装上阵’的;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那种只顾经济发展,不管或忽视社会管理问题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已经走不下去了。” 沈奎说。
但“开发区管委会只是一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行政区的很多事情,它管不下来。合并之后就方便处理这些事情。”周振邦说,“因此开发区和行政区合并,是客观需要、是管理体制创新的问题。”
6. 体制:向左走?向右走?
在记者的采访中,无论是开发区人、还是专家学者,“小政府、大社会;小机构、大服务”的“体制创新”都被视为开发区成功的首要经验。
“开发区20多年来不断挣脱各种陈旧观念的束缚,克服有形无形的困难,为自身前进拓出空间,每走一步都要靠锐意改革,甚至可以说,改革比开放困难要大得多。尤其在前10年,改革的任务比开放占去开发区更大更多的精力。”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副巡视员王恺说。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研究室主任黄承祀曾经数过,改革开发之初,一个小县城,审批一个项目,行政机关一共敲了64个公章。也由此,在开发区诞生了“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一窗口收费”服务体系。
如果对中国开发区的管理体制进行总结就会发现,自1984年以来,首批14个国家级开发区除上海的3个以外,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建立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管理体制,这也成为此后其他开发区的普遍选择。
这种管理体制模式是,以地方人大和政府的特别授权,组建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代表市政府管理开发区。在形式上,开发区管委会是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以一个“委”的建制出现。
对此,王恺在其《走出孤岛》一书中分析,“在一个没有居民或居民很少、素质很差的地区,一开始就实行传统管理体制,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切实际的。而靠政府的派出机构来实现区域的快速启动,以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设计初衷,当时只能采取这种不规范的、创新的管理体制”。
但亦有学者指出,就国家层面而言,尚没有专门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各类“开发区管委会”给予法律地位定位,把“开发区管委会”定位为“人民政府派出机构”找不到宪法和有关组织法上的依据,也缺乏理论支撑,甚至因此断言,开发区管委会“本质是临时机构”。
“没有立法,开发区就天天做着不违法、但违规的事情。”中国开发区协会副秘书长周振邦说。
由此引出了对开发区存在根源的探讨。
肖金成认为,特区开发区存在的条件是:整个国家在宏观导向上要由封闭走向开放。如果整个国家是开放的,搞一个“孤岛”,整个社会环境是不太适应的,效果也不会太好,因为跟现行法律相抵触,就很难有生命力;如果从封闭走向开放,作为一种探索、尝试,将来的法律制度要做相应的修改,那么它虽然短期内不一致,但最终是会一致起来的。所以,“特区开发区最大的优惠政策是‘先行先试’。没有这四个字,是搞不成的”。
“我国将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该借鉴开发区的经验,而不是开发区向政府体制复归——衙门林立,互相制约。”肖金成说。
但在开发区与行政区合并后,“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创新精髓能否被成功保留,面临诸多挑战。
“中国现在进入了‘后开发区时代’,中国的开发区更多都在选择城市化。单就城市化来说没有问题,关键是这种城市化过程中会选择怎样的管理体制,如果在这种真政府的管理体制中,继承了原来开发区探索出来的高效的模式,那变成真政府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仅仅是将旧的体制复制过来,那就是退步。”王恺告诉记者,“一个项目进来还是需要盖20个章,层层审批,那改还不如不改”。
“开发区人”并非没做过立法以固定开发区经验的努力。
2004年,开发区成立20周年时,“开发区人”准备推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出台,通过行政法规将‘小政府运作园区’的开发区体制经验固定下来,以保证效率。但《条例》到了最后的部委会审环节时,出现不同意见,被迫搁置。2009年,开发区成立25周年时,业界原计划再次推动《经开区条例》出台,不巧遭遇金融危机,又被搁置。
目前,取得的唯一进展的是,2005年3月21日,国务院公布的15号文件——《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提高发展水平若干意见的通知》,确定了15条方针,被业界视为“准开发区条例”。
“要立法,不简单。”周振邦说。
“从长远来说,《开发区条例》出台的问题是会解决的,但短期内取得一致有困难。”陈青洲说,“这跟国家的政治改革进程有关……但上层建筑滞后,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这个已从漕河泾开发区领导岗位退居二线的“老开发区”,至今对此念念不忘。“我们国家应该是个法治社会,开发区成立27年了,应该有个法律来保驾护航。”
7. 开发区的终结?
在众多的开发区开始寻求向城市化发展转型的时候,开发区时代在中国是否面临终结呢?
“开发区和行政区已经合并了,为什么还叫开发区?”周振邦反问。
“因为开发区还有改革的使命。”他自问自答,“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载体还是在开发区。”
“如果开发区不做,国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会落空;如果开发区都做不成,其他地方更难。”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武廷海亦持类似观点。
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太大,各地区发展阶段和水平并不一致”。当东部的开发区已经趋于稳定推进的阶段时,西部的开发区建设依旧如火如荼。仅在去年,国家就一次性升级了62家经济技术开发区,超过过去26年的总和,使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总数达到116家。其中,大多位于中西部地区。
“现在开发区已经没什么政策优势了,发展靠的是实力,重视的是软实力、无形价值、内涵的提升。”周振邦认为,对中西部地区而言,国家级开发区具有品牌效应,可以提升当地的城市形象,提供发展动力。
除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地方兴办的各种各样的开发区更是难以统计。
1992年以来,曾兴起三波“开发区热”,省、市、县,甚至乡镇都办起了“开发区”;名目也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达到6000多家。为此,中央于1993年、1998年、2003年进行了3次清理整顿。结果是,“清理——反弹”。
“之所以出现三次‘开发区热’,就是因为开发区是对改善投资环境、招商引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建设都非常有利的模式——集中在开发区里搞工业总比‘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发展方式好,开发区这种模式的优势和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冲动结合在一起了。”作为国土资源部专家组成员参与了2003年开发区清理整顿工作的肖金成说。
在王恺看来,从发展体制创新角度讲,中国的开发区模式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进行发展模式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寻求经济发展的模式借鉴,包括俄罗斯、东南亚国家以及非洲一些国家等,开发区模式可谓“方兴未艾”。
周振邦认为,中国的开发区事业还要走20年、30年,甚至更久。“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逐步推进和完成,开发区的使命就完成了,留下的是一个个产业新城。”
纵然如此,今天的开发区与1984年的开发区已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做规划时,开发区就是按多功能区来做的,而不是单一功能。”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说。据他介绍,在邓小平的故乡——内陆小城广安,规划面积100多平方公里的开发区内,甚至还有森林公园!
“单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概念已成过去式。”周伟林说。
• 中国角型毛巾架行业运营态势与投资潜力研究报告(2018-2023)
• 中国直接挡轴市场深度研究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2021-2023)
• 2018-2023年KTV专用触摸屏市场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
• 中国回流式高细度粉碎机市场深度调研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3)
• 2018-2023年中国原色瓦楞纸行业市场深度研究及发展策略预测报告
• 中国雪白深效精华液市场深度调研及战略研究报告(2018-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