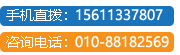
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中诚广场”大戏已告收场。作为一件被执行标的,从1996年被海南省高院查封,到2005年最高法院批复同意相关执行方案,十年间,中诚广场成为法院执行现实生态下的一个样本。
2001年至2007年9月,杨贤才在广东省高院执行局局长位置上任职6年。在中诚广场一案中,其在潮汕同乡黄松有的协同下,通过控制执行标的转卖和改变执行状态而获利颇丰。
在法院认定的对杨贤才的十二项指控中,共有八项涉及“执行难”。2003年下半年起,杨贤才在广东省高院首创的执行新举措——将下级法院难以执行的案件统一“打包”指定执行,让其声名远播同时亦可渔利其中。
法院认定,1996年至2008年春节,杨贤才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赃款合计1183万余元。另外,杨贤才对价值人民币1695万余元的其他家庭财产无法说明来源。
因案件执行而落马者并非只有杨贤才、黄松有二人,与中诚广场案有干系的海南省高级法院执行庭原庭长马升、广州中级法院执行庭原庭长刘宽等多人亦因此身陷囹圄。
上述法院执行系统官员共同之处在于,监督缺失之下,利用法院执行系统的权力和现行执行制度的漏洞,通过控制被执行标的评估、拍卖、变卖或转让的法律流程,调节执行案件的快慢节奏而寻租其中。
集权之弊
据法院判决书,杨贤才被认定的一项指控是,收受广东东莞慧谷集团(下称东莞慧谷)董事长张炳光30万港元的“感谢费”。
早在1999年,东莞慧谷与香港恒富集团在合作开发房地产时发生纠纷,随后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裁定东莞惠谷胜诉。但直至2003年,东莞慧谷的债权仍然未被执行。后该集团董事长张炳光找到杨贤才寻求帮助,后者答应并“笑纳”前者送上的10万港元。
随后,杨贤才指定此案从深圳转到广州黄浦区法院执行。但虽有其介入,此案执行工作仍然不顺,恼火之余,杨贤才再度移交此案,指定由佛山市中院执行。历时8年,2007年该案执行完毕,张炳光通过朋友再送给杨贤才20万港元。
这番周折的背后是法院执行难的现实背景。1999年,中央11号文件特别提到“执行难”,并概括为四句话:“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
随后全国法院范围内掀起的“执行风暴”中,广东省高院推出了五项措施解决执行难。其中大力推行的“提级、交叉、指定执行”的措施,以及“限高消费令”,被普遍认为是杨贤才的政绩。而其主张推行的特殊案件由上级法院“打包”统一指定执行的制度,也取得很大成效。很多疑难执行案件得解,杨贤才亦因此被称为“铁腕执行局长”。
“执行难”背后有诸多因素,地方保护主义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这种受制于地方党政领导的司法格局,客观上削减了上级法院的监督权。而通过上级法院的集权,对一些疑难案件提级执行或者指定异地法院执行,很大程度上的确可以回避地方保护主义。
但这种上级法院集权的制度,客观上造成杨贤才个人完成了集权的过程,在缺乏严格监督之下,为其带来新的更为便利的寻租机会。
海南省高院原执行庭庭长马升,曾参与广州中诚广场案件的执行,其落马亦与此种制度之弊有关。
1999年2月,香港辉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香港辉景)向法院申请执行对海南珠江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海南珠江)的债权,价值7000多万元,其中包括查封后者拥有的东湖大酒店的经营管理权。海南省高院对东湖大酒店未予查封,仅对海南珠江价值3000多万元的资产进行执行。虽然香港辉景多次申请查封东湖大酒店,但由于马升迟迟不表态,执行工作无法开展。
直到香港辉景负责人呈上一枚价值2.6万元的钻戒后,马升才在申请报告书上作出了“应考虑查封东湖酒店三权”的批示,并得以顺利执行。
监督失效
据《财经》记者调查,除中诚广场案件外的其余所有指控,均为杨贤才主动交代而来。正基于此,其被认定有自首情节,从而得以轻判。
这一自首情节也表明,“提级、交叉、指定执行”的措施带来更为便利隐蔽的寻租条件。
在杨贤才被认定的指控中,多数属当事人为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顺利得到法院执行,求助杨贤才后表示感谢而“行贿”。除东莞慧谷案和律师许俊宏介绍行贿案(参见本期《财经》“关键人”杨贤才)之外,对杨贤才的指控还包括:
1996年,深圳中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深圳中盛)与深圳旅游公司发生诉讼,后由广东省高级法院调解结案,但一直未能实现债权。2001年,深圳中盛总经理刘耀找到杨贤才,后者协调后,2003年债权被顺利执行。2004年,刘耀送给杨贤才20万元“感谢费”。
1996年,铁道部第二工程局东莞第二工程总队负责人黄某因承建东莞金湖花园与合作方发生纠纷,案件在执行过程中,黄某找到杨贤才,杨将该案指定到广州铁路运输中院,案件执行终结后,黄某送给杨10万元。
1999年,泛华工程公司深圳分公司(下称泛华深圳)与深圳国都集团因购房发生纠纷,前者胜诉后,案件在执行时,后者的另一债权人深圳怡和公司向广东省高院提出执行异议。泛华深圳担心法院偏袒深圳怡和公司,遂找到杨贤才,杨允诺帮忙。泛华深圳总经理林贞平送给其10万港元,之后顺利实现债权。
2001年至2007年间,广东融通投资公司负责人纪鸿涛先后代理多起执行案件,在同乡杨贤才的协调下,均顺利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实现了债权。
2002年,深圳商人周昭禄与深圳金田公司共同开发金田广场时产生纠纷。前者通过朋友陈某找到杨贤才希望实现债权,杨贤才指点周进行仲裁胜诉后,将该案指定到广州铁路运输中院执行。2006年上半年,在实现部分债权后,陈某送给杨贤才10万元。
2006年,律师陈卓伦在代理一执行案时认为广州珠海区法院执行不力,经杨贤才帮助后该案顺利执行。2007年,陈卓伦送给杨贤才12万元。
广东某中院执行局法官告诉《财经》记者,“提级、交叉、指定执行”的措施并未有错,决策者获得寻租机会的根源在于,强制执行制度缺乏有效监督措施。
该法官认为,广义上看对执行的监督范围很大,包括人大监督、检察监督、群众监督、当事人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文件中曾单列一节《执行监督》,但被确定下来的监督方式只有一种:上级法院的监督。《民事诉讼法》中也缺少对执行行为监督的规定。
目前在学界中争议最大的是,是否应在执行中引入“检察监督”。此前,在深圳市中院原副院长裴洪泉等5名负责执行的法官案发后,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加强人民法院民事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在地方法规中提出对法院执行工作的“检察监督”。
但此举最终流产,原因是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的反对。其理由是,《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而法院的执行权不是“民事审判活动”,因此,检察院只能监督法院的审判活动,不能监督执行。
而此前最高法院1995年8月10日颁发的《关于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和1996年8月8日颁发的《关于检察机关对先予执行的民事裁定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审理问题的批复》司法解释中,对民事检察监督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的适用几乎全部排斥,至今这一问题未能解决。
腐案高发环节
由于缺乏有效监督,法院在执行工作的最初——评估、拍卖阶段,亦成为腐败的高发环节。
2001年,深圳市南山区法院对深圳福田南路一宗土地进行查封并拍卖,深圳大景源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深圳大景源)欲取得土地的使用权,该公司总经理黎智华从杨贤才处打听到案情。
随后,深圳大景源与该宗土地的债权人签订虚假《借款协议书》,从而介入执行案件。最终在杨贤才协调之下,深圳大景源如愿获得土地使用权。黎智华为表示感谢,给杨贤才送上600万港元,存到杨朋友户头,用于其在香港炒股。
而在中诚广场一案中,2002年,广州市中院委托数家拍卖行进行公开拍卖的准备工作期间,该院原执行庭庭长刘宽因拍卖受贿而落马。但最后,中诚广场的执行程序还是在黄松有和杨贤才的控制下被指定变卖,而不是拍卖。
而黄松有贪污罪也由此环节而来。1997年,黄松有任院长的广东湛江中院办有一家“三产”公司,专门承担法院的拍卖项目,并由法院工作人员承包。当时,湛江一拍卖公司找到黄松有要求承接法院的一个拍卖项目,如愿以偿后,该拍卖行给湛江中院“回扣”近千万元。其中308万元被黄松有和他人私分,黄松有得款120万元。
与杨贤才和黄松有相类似,重庆市高院原主管执行的副院长张、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落马均与被执行标的的拍卖程序有关,而四川省高院执行局原局长罗书平,同样落马于烂尾楼的复工和拍卖程序。
此环节腐败案频发,根源于司法拍卖行为缺少有效的外部监督以及事后的有效救济。按相关司法解释,因为司法拍卖导致的纠纷,不具备可诉性。这意味着利益受损方丧失了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
而由于估价和拍卖的利润获取均是依据标的物价值、按照一定比例收取佣金,受利益的驱动,评估机构会故意抬高评估价格,拍卖机构则希望尽量降低评估价格,以便尽快拍卖成交获取佣金。由于其中的裁量权属于法院,其中滋生的寻租空间,使得诸如杨贤才、罗书平等有决策权力者“前腐后继”。
(本文见《财经》杂志)
• 中国角型毛巾架行业运营态势与投资潜力研究报告(2018-2023)
• 中国直接挡轴市场深度研究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2021-2023)
• 2018-2023年KTV专用触摸屏市场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
• 中国回流式高细度粉碎机市场深度调研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3)
• 2018-2023年中国原色瓦楞纸行业市场深度研究及发展策略预测报告
• 中国雪白深效精华液市场深度调研及战略研究报告(2018-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