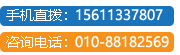

永昌县东寨镇头坝村六社,大年除夕前家家大门贴上了对联,但不少门户紧锁,村头空寂冷清。赵莉 摄
全村22户人家,已经有10户院落成了空宅子,剩下的12户人家中,大多留守的都已是年过六旬的老人。面对这个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现在却正在加速衰老和凋敝的村庄,闫有吉怀揣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愫……
一个家族的除夕聚会
2月9日,农历除夕。
大清早呼啸不断的山风预示着这一天的晴好天气。在永昌县东寨镇头坝村六社,63岁的闫有吉起了个大早、扫院子、烫浆糊,准备早饭,忙得不可开交,丈夫姜望宁则将果盘、糖果瓜子等摆放到茶几上,又郑重地取出常年派不上用场的茶杯,洗去灰尘,放上茶叶。火炉里的炭火烧得正旺,即将烧开的热水发出“咕咕”的声响,这个生活在祁连山脚下的庄户人家,一年中难得的热闹马上到来。
上午10时30分,大门外的汽车喇叭声打破了宁静,姜望宁和闫有吉迎了出去,一大群人唤着“哥哥”“嫂子”“叔叔”“婶婶”“爷爷”“奶奶”涌进了院子。客人中既有姜望宁的堂兄弟,也有子侄乃至孙子辈,大家相互问候、寒暄,提前说着过年的吉祥话,一时间的欢声笑语让这座绝大部分时间里孤寂的“两人”院落生趣四溢。
这些亲戚曾经都是姜望宁的左邻右舍,现在,他们都去了永昌县城或者是更大更远的城市生活,除夕这天返乡,一则是为了给留在村里的老宅子贴对联,二来是为了共同祭拜先人。“每一年就数今天人聚得最齐全,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也要上坟,不过只有住在县城里的人回来,再远的就不来了。”闫有吉说着一年中能数得着的几个热闹日子。由于整个家族中只有姜望宁和闫有吉还生活在村里,两位老人的家自然也就成了族人们每次相聚的地方。
此刻,整个家族的男人们聚在一起,一边剪裁对联,一边讨论着一年来的家国大事,许久不见面的女人们仍然有拉扯不完的家长里短,孩子们相互追逐嬉戏。闫有吉有些手忙脚乱,近几年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忘性便也跟着增大,常常是前一分钟还在使用的家什,后一分钟便不记得放在哪里,忽然要操持这么多人的家族聚会,她看起来力不从心:“平时两个人凑合惯了,人一多就慌了,忘东忘西的。”
吃完了早饭,大家开始相互帮忙贴对联。长久空置的老宅子里落满了灰尘,有的院子里已经长出荒草,也没有必要清理,只需在房门上贴上对联、“福”字,然后再放一串鞭炮,就算完事。
“每家都有这么多的房门,都挨个儿贴,真麻烦,城里只要一副对联往门上一贴就了事了。”一名年轻人皱着眉头。在他看来,城里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和便利的生活设施,正是更多村里人涌进城市的主要原因:“小区里有商店,门口有菜市场,出门就可以坐车,孩子在假期里可以找到补习老师,上学的时候不用顶风冒雪地跋涉。不像回到村里,连上个厕所都会被冻屁股。”
两个多小时后,闫有吉已经准备好了祭拜所需的食物,男人们去祭祖,女人们开始准备午饭。下午2时许吃完午饭,这个家族一年一次的聚会就算完结,大家与姜望宁和闫有吉握手道别,叮嘱他们好好保重身体,然后钻进各自的车里绝尘而去,他们赶回城里准备各自家里的年夜饭。
院落的热闹像潮水般忽地涌来,又忽地退去,只留下一桌还来不及收拾清洗的餐具。
一个村庄的片刻热闹
事实上,闫有吉家最热闹的时刻,也正是整个村子最热闹的时刻。那些平日里都只有“铁将军”把门的空宅子里,忽然就多出了许多出入的身影,生了锈的铁门上,也都贴上了崭新的对联和喜庆的“福”字,鞭炮声不时在村子的每一个方位炸响,弥漫开来的硝烟味传递着空气中辞旧岁迎新春的讯息。
“就贴对联这么一阵子,过一会就散啦。”对于突如其来的热闹和它同样突兀地消失,闫有吉早就习以为常。
东寨镇头坝村六社是一个距离永昌县城大约12公里的自然村。在闫有吉的记忆里,自从嫁过来,这里就是一个有着22户人家的“大庄子”,每户人家的人口数从几口到十几口不等。以前人丁兴旺的时候,每逢过年,光是村里的女人们相互帮忙做馍馍,都需要好几天。每年一进腊月,人们就开始杀年猪、组社火、排小戏,一直要闹到正月出头。庄稼人一年忙到头,最讲究的就是正月,什么大事也比不上过年重要,经常是头坝村的某一个村里搭了戏台,整个行政村的乡亲不论男女老少,都赶过去看戏捧场。
但是这样的记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定格了。闫有吉说不上是具体哪一年,村子里开始有年轻人外出打工,或者是上大学。出去的人没有再回来,反而带动着村里更多的人外出了,先是20多岁的年轻人出去了,后来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跟着出去了。人们奔赴或远或近的城市去讨生活,年轻一点的直接在外面安了家,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则用挣来的钱在永昌县城里买了房子,将老人和孩子接去居住,村里的老宅子便空置了。
事实上,搬到永昌县城里生活的人家,并没有完全剥离对土地的依赖,他们依然会在每年农忙的季节抽几天时间回到村里,播种、浇水或者收割,然后返回县城,靠着打零工为生。除了逢年过节的时候会回到村子里转一圈,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里,就基本割裂了与这座村庄的联系。
非农非城的身份,给他们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昔日年轻的村庄日渐老去乃至衰败。
“年轻人们还在依赖土地,但是他们已经不再眷恋土地。”姜望宁说。
离开的人家越来越多,村里的空宅子也一年多过一年。到今年春节的时候,原有的22户人家已经空了10户常年无人居住,在剩下的12户人家中,绝大部分生活的也都是像姜望宁和闫有吉这样年过六旬的留守老人,仅有极个别人家里还有因身体原因不能外出打工的中年人。
“和我们一样,都老啦!”每次一说到自己从出生开始就一直生活着的村庄,沉默寡言的姜望宁便会发出这样无力的叹息。
不过姜望宁时常担心,即便是这样短暂的热闹,恐怕也维系不了太久的时间。“现在还回村里祭祖、贴对联的,都是家里有老人的。老人们有这份情,愿意这样做,儿孙们自然也就跟着来了。等老人没了,年轻人们恐怕不愿再费这样的事了。”
闫有吉用早已失去用武之地的上百副碗筷来印证丈夫的担心不无道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套家当为全村办过不知道多少场男婚女嫁的喜事。“那时候庄子里人多,红白喜事儿也多,大家都是在自家办流水席。每次不管谁家遇到红白喜事,都要向全村的人借碗筷,事办完了再一家一家还回去。我实在觉着麻烦,何况那时候我家里人口多,办事儿的次数也多,就干脆咬咬牙自己置了一套办席的家当。”在当时,闫有吉的决定算是一个大手笔,而这套家当,则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充当了全村办喜事的公共餐具。
如今,这些家当被堆放在一间偏僻的厢房里,因为失去了昔日的用武之地而落满灰尘。近几年来,村子里几乎难有婚嫁之喜,外出的年轻人不会再回到村里来办喜事,即使遇到有老人过世,由于村庄日益凋敝,人丁稀少,已经用不了这许多的家什。
一份难舍的复杂情愫
鞭炮声在晌午过后逐渐散去,村庄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初春的阳光带着寒意,将一扇扇贴着对联、挂着铁锁的大门照成了清冷的特写,偶尔的几声狗吠依旧是整个村庄里最有活力的声响。闫有吉疲倦地躺在了炕上,她要睡上一觉,才能恢复忙碌了大半天的劳累。
83岁的高惠珍老人,则开始为自己准备年夜饭。她洗了几个土豆,放进锅里搭在火炉上蒸煮。等土豆煮熟后碾成土豆泥,再剁上些肉和韭菜,就是自己最爱吃的饺子馅,但是揉面和擀饺子皮的工序,对于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仍然有些困难。
高惠珍孤独地守坐在火炉旁边,看着锅里的水蒸气氤氲开来,浸润过额头深深浅浅的褶皱,沾染在墙上那块红色的“四世同堂”的匾额上。那是两年前老伴去世时,家里的子侄孙子们按照当地的传统制作赠送的,在“四世同堂”四个金色的大字下面,二三十个从子侄到曾孙的后辈们的名字缀成了长长的一串。
“这些都是家里男人们的名字,女人们都还没有算进去呢!”高惠珍有些骄傲,她一生育有7个子女,夫家亦是庄里的大户。只是现在,大部分时间陪伴在她身边唯一的活物,就只剩下院子里的一只小黄狗。
高惠珍是村子里年纪最大的老人,子女们几乎都搬到城里生活去了。老伴去世后,也有儿子将高惠珍接到县城里去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是出于对城里种种生活习惯的不适应,几个月后她又固执地回到了村里。儿女们没有办法,只好每隔一段时间就回村为母亲置办吃穿用度,洗衣晒被,其余的时间,也能只靠高惠珍自给自足。
“城里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好,庄稼人,总是脚要踩着土地,心里才会觉得踏实。”高惠珍说。
但闫有吉并不这样认为,在她看来,城里的楼房至少代表着一种体面的生活和某种形式上的成功:“能在城里买楼房的,都是有出息的或者有钱人。”因此,她为几个女儿都已经在县城里有了楼房而感到一丝优越,同时又急切地盼望着儿子也能尽快地将自己和丈夫姜望宁接到省城去生活。
“最多再有一年,说不上是半年,我们也就进城了,等儿子在城里的工作和家庭再稍微稳定一点,我们也就搬走了。”对于未来的城市生活,闫有吉有着迫不及待的渴望。
但是在春节联欢晚会开始前,当头一天才刚刚从省城回到家的儿子开始和父亲姜望宁商量,要不要在今年春播开始前就找人把土地出租出去时,闫有吉却忽然愣住了,她像是自言自语式地发问:“人都走了,房子也空了,庄子里会不会有一天连一个人都没有了?再过上十几二十年,还会不会有人再回到村里的老宅子,上一炷香,捧一抔土?”(兰州晨报 记者 赵莉)
• 中国角型毛巾架行业运营态势与投资潜力研究报告(2018-2023)
• 中国直接挡轴市场深度研究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2021-2023)
• 2018-2023年KTV专用触摸屏市场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
• 中国回流式高细度粉碎机市场深度调研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3)
• 2018-2023年中国原色瓦楞纸行业市场深度研究及发展策略预测报告
• 中国雪白深效精华液市场深度调研及战略研究报告(2018-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