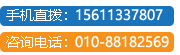
河南兰考事件发生之前,由民间收养机构、个人抚养代养的50多万名孤儿与类似袁厉害的爱心妈妈共同生活,然而一场大火过后,民间收养机构四面楚歌,一些民间收养机构除面临身份注册难、资金筹集无路的困境外,还需面临机构被遣散的尴尬情况。
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民间收养机构
中国现有孤儿共约61.5万名,其中由民政部门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有10.9万名,由亲属养育、其他监护人抚养和一些个人、民间机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
河南兰考“袁厉害事件”发生后,这些平日被民政部门默许存在的民间收养机构,在最近一段时间,面临的却是被遣散的尴尬局面。
多地民间收养机构或被遣散
袁厉害的收养所发生火灾后,一些与袁厉害情况类似的“爱心妈妈”担心,只要这样的事情发生一起,类似的公益机构想“活”下来就更难了。
1月14日下午,当朱智红接到河南省平顶山市曙光街办事处的一张通知书时,脑子里一片空白。
她觉得自己近10年的努力又回到了原点。
通知书上认定,朱智红及其家人于2007年创办的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李庄新村“爱之家”孤儿寄养点是一个非法机构,要求她停止“爱之家”的一切活动,并将寄养点中的18名孤残病儿退还到当地福利院中,如不执行,将前往整顿,并强行搬走所有东西。
自1月4日,河南省兰考县袁厉害自办的民间孤儿收养所发生火灾后,一些“爱心妈妈”就坦言,只要这样的事情发生一起,类似的公益机构想“活”下来就更难了。
1月6日,民政部正式下发《关于主动加强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主动做好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的管理工作,用一个月时间,组织力量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进行排查,坚决消除安全隐患。
河北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是一家民间收养机构,其负责人李利娟说,兰考大火后,武安民政部门更加不放心她和爱心村内近50名孩子,要求她改造家里的厨房以及门外沿山坡的地方加建护栏等有可能出现事故的地方。
这种结果让李利娟长舒了一口气,她曾担心民政部门要求她将孩子全部送回福利院。
各地对安全隐患的标准不一,对民间收养机构的去留标准也不尽相同。
与袁厉害的收养模式不同,“爱之家”更偏重于寄养,这里的多数孩子是平顶山市内各福利院送来的孤残病儿,由朱智红联络省外的各基金会对这些孩子进行医疗救助及术后养护。康复后,再由朱智红将孩子送回福利院。
朱智红说,在“爱之家”的医疗救助之前,平顶山市福利院没有一个孩子被收养,经过救治后,最近几年,先后有一百多个孩子被国内外的家庭收养。
从最初朱智红求着福利院让自己把重病的孩子带走救治,到现在与周边七八家福利院建立长期合作,朱智红觉得自己也推动了福利院工作的改革。
当朱智红收到遣散通知后,其实她并不清楚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朱智红表示,1月11日下午,还曾有河南省民政厅及平顶山市民政局的相关负责人前往“爱之家”,领导们一致认为“爱之家”对这些孤残病儿的照顾很专业。
朱智红回忆,有领导指着“爱之家”中的孩子说,“看,这里很多孩子都是咱福利院主动送来的,说明咱福利院里确实存在问题”。
可即便这样,爱之家仍面临被解散的困境,而在朱智红接到通知书后,多地民间收养机构均收到了遣散的通知。
123下一页
民间收养机构身份之困
由于上面没有政策,平顶山市社会福利科一直不知道参照什么样的办法给这样的组织登记注册。
曾任河南省平顶山新华区民政局的陈局长表示,如果不是河南省兰考县的那场大火,他还打算在今年春节前去探望爱之家孤残病儿寄养点的孩子们。
他表示,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区民政局只是听说孩子们是市福利院寄养在这里的,也不知道寄养之后,孩子被转移到哪里去看病,更不清楚治疗结束后,孩子又被送到了哪里,整个监管均呈空白。
其实,朱智红从2010年起,就数次前往市民政部门,报材料跑注册。得到的答复不是根据相关规定,民间不允许成立福利院收养孤儿,就是出于害怕她拐卖孩子、贩卖婴儿,民政部门不予办理登记注册手续。
可朱智红表示,自己根本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寄养和收养完全是两个概念,在这个寄养点中,孩子在此养育的时间不会超过3个月。
朱智红说,1月11日,新华区民政局及平顶山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及省民政厅的领导在排查民间收养机构时,也到爱之家来了解情况,并表示只要将爱之家这个民间组织进行注册,规范起来,民政部门可对其进行监管即可让爱之家继续存在,这让朱智红眼前一亮。
1月14日,朱智红的二姐一早就前往市民政局,得到的答案却又变成了再观望一阵子,等以后国家出台了明确的政策法案,再依法办理。
平顶山市社会福利科刘科长表示,其实他们很早就知道爱之家这个民间寄养点,逢年过节,民政部门也会为他们送去慰问品,他们也希望给予爱之家一些政策上的支持,但刘科长不停地解释称,由于上面没有政策,社团科一直不知道参照什么样的办法给这样的组织登记注册。
按照我国《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民间组织注册必须要有主管单位,否则就是“非法”。
缺乏国家经济支持的收养机构
民间救助机构的优势是程序简洁、救助迅速,但最大困难就是高昂的治疗费用。
没有身份,直接导致的问题就是机构资金来源的不稳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表示,事实上对很多民间慈善组织来说,可调动的社会资源有限,仅凭善心做慈善,缺乏规范和长效运行机制,是他们遇到的普遍困境。
最近,北京“天使之家”又将面临创办后的第五次搬家,目前“天使之家”挂靠在“儿童希望基金会”的名下,但更多的资金来源还是依靠社会募集。而在几年的运作过程中,“天使之家”也曾数次面临停水、停电,以及重新选址的难题。
对于朱智红来说,最难解决的就是高昂的医疗费。先心病的患儿在出生一周内最好进行手术,肛门闭锁的孩子应在出生后3至7天进行手术,还有很多病种,在发现后的24小时内治疗最佳,有时上午接到的患儿,下午就有可能在北京的某家医院中进行治疗了。朱智红说,这就是民间救助机构的优势,程序简洁、救助迅速,但最大困难就是治疗费用。
朱智红的资金来源主要靠网上募捐。
有的孩子有心衰的情况,上呼吸机的费用每天要一千元,她曾为了让一个孩子用呼吸机,向福利院寻求帮助,但福利院最终选择放弃治疗。
民间收养机构出路的地方探索
如果有足够的物资,朱智红说,她能救助更多的孩子。今年,她的目标就是想争取机构注册成功。
“我希望相关政策能尽快完善,让这些孩子们享受与公办福利院同样的待遇,让孩子们更有公平感”,而李利娟表示,这也是很多民间收养机构创办人共同的愿望。
从1996年收养第一个四川籍孤儿开始,截至2013年1月初,李利娟已经收养了54个孩子,其中48个孩子是孤儿或弃婴,6个是其父母无抚养能力的孩子。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48个孩子全部上了户口,以李利娟为法人代表的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也已经注册。
2012年年初,“转正”的安徽省颍上县王家玉孤儿院,让李利娟看到了希望,现在王家玉孤儿院已经成为颍上县社会儿童福利院,2011年该孤儿院被纳入国家福利体系,未满18岁的孤儿都能享受到由国家、省级和地方三级财政配给的每人每月1000元补助。
这让李利娟看到了希望,她一直盼望着能有一所高标准、设施完善的福利院,能给那些孤残儿童创造最好的生活条件。
目前,经武安县相关部门协调后,已经为李利娟提出的民办福利院选好地址,规划用地50亩,由政府筹划。资金方面,将由政府、民间集资和李利娟个人三方解决。
武安县相关部门已经为李利娟提出的民办福利院选好地址,由政府筹划。资金将由政府、民间集资和李利娟个人三方解决。
上一页123下一页
□案例
一个官办福利院的改革之路
一群乳娘、一群孤残儿童,让山西大同散岔村成为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模式的发祥地。但随着社会发展,“大同模式”的乳娘村却在不断缩减,从建国初期的38个锐减至今日仅剩散岔村还在孤独地坚守。
面对新时期的历史条件,领孤残儿童抚养模式改革之先的大同福利院,正在进行一场从农村到城市、从寄养到寄宿的全面转型。
“我一直想养两个孩子,之前工作没有条件,现在退休了,可以全职照顾孩子了。”大同市散岔村的张仲桃和老伴儿都是退休教师,从2002年起,就代养大同福利院的孤残儿童,已代养了十多个孩子,大部分身有残疾。
在散岔村,代福利院抚养孤儿是件很普通的事。从上世纪60年代,这个贫困村相继抚养了1300多名孤残儿童,其中95%身患残疾。至今还有90多户人家寄养着100余名孤残儿童。
为福利院代养孤儿的乳娘,一部分是类似张仲桃一样,有着较好的经济条件,自愿为抚养孩子尽一份力,还有一部分贫困家庭靠每个孩子每个月的政府补助结余帮助改善生活。
“从最开始的一个月给十几斤小米到几元钱、十几元钱……直到现在,每个孤儿每个月能有近1000元的生活费。”村支部王书记说。
不过,随着社会发展、物价上涨及人们观念的改变,福利院的补助正逐步失去诱惑,相比于寄养孩子在家所需要付出的精力,更多的人选择外出打工。时至今日,38个寄养村仅剩一个散岔村在坚守。
与农村寄养同步展开的还有城市寄养。“无论在教育还是医疗方面,城市的硬件条件要比农村好很多。”大同福利院一丁姓副院长坦言。
由于城市寄养成本较高,除了补助略高外,福利院还会提供棉被、衣服等生活用品。
遗憾的是,多数城市居民在代养意愿上仍不强烈。
上海财经大学在一份2011年针对孤残儿童家庭寄养的调研报告显示这与物价上涨、人们价值观及生活习惯的改变、精力不足等有关。报告称,家庭寄养制度从传统的农村模式向城市转变是个漫长的过程,会经历许多“过渡阶段”。
2011年7月,大同福利院找到了这个“过渡阶段”,一种新的养育模式——“寄宿家庭”在院里悄然展开。
在福利院里,十多个“模拟家庭”迅速建立起来,每户家庭由一对寄宿夫妻负责养育5到6名孤残儿童。妻子负责照顾家庭,丈夫白天可在外工作,晚上回“家”和孩子们一起生活。周一到周五,家长将孩子送到福利院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和早期教育,中午、晚上将孩子接回,享受父母关爱。
所有的寄宿夫妻都是福利院从社会上招募来的,除了要求其身体健康,有爱心外,还规定不允许夫妻自家小孩与孤残儿童一起住在“模拟家庭”中。
福利院还将对寄宿夫妻进行严格培训,合格后发给寄宿证,并据寄养儿童数量向家庭发放生活费。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褚松燕认为如果有相应的利益机制、情感机制等来保障,这种模拟家庭模式不失为一种穷尽收养之后的选择。政府也应提供实操性政策和经费支持,并逐步完善收养法、寄养规定等,在不缺位、不越位的情况下,做有效的制度提供者。
收养难在领养人要求高
记者:多数收养家庭认为,现行的收养法门槛过高,你如何看待?
童小军:事实上,我们的收养法所限定的收养条件并不高,但家长在收养孩子的时候,提出的条件很苛刻,包括长相、智力、血型、星座、属相等。
记者:外国人从中国领养的孩子大部分是有特殊需求的,但在我们国家并不是这样的情况,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童小军:我们现在促进孩子拥有家庭的服务并不规范,从理念上讲,国内家庭收养孩子更多的是考虑收养人的需求,孩子的未来是其次的。
而国外的收养人,会在考虑自身需求的同时,兼顾考虑孩子的未来,并且有相当数量的收养人纯粹就是为了仁爱,帮助生活困苦的孩子,他们希望通过收养,让这些孩子获得幸福和健康成长。国外这样的领养家庭比国内多得多。
记者:在收养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存在缺失的地方?
童小军:我们没有专业人员对这些领养家庭进行专业评估,包括领养前对领养家庭和孩子的评估和准备、领养过程中的协调,以及对孩子进入领养家庭之后的追踪及监督。
记者:官办福利机构与民间福利机构相比,在养育孤儿方面,哪个更有优势?
童小军:从权力责任的角度,政府绝对占有优势。但是,这个判断的前提是无论官办还是民办,都是从儿童的利益出发的。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有责任。
如果不是官办机构,就应该对民间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包括对开办资质的审核和对养育服务品质的监督,应当分清楚在孤儿养育领域里政府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社会如何参与进来。
家庭失能突显政府监管缺失
记者:哪些应当是政府承担的责任,但缺位了?
童小军:要保障儿童权利,必须把儿童当作一个整体,国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家庭失能的情况下,国家首先应对失能家庭提供补充,给予福利支持。
一旦家庭消失,政府应承担起养育孩子的责任。孩子们应该在一个可靠、有保障的国家监护环境里得到养育。
但事实上政府在替代照顾这一方面,无论是从立法还是机制建设,以及整个服务的监督评估等都不完善,比如现在一些孤儿的爷爷奶奶,并不愿意自己的孙子或孙女被领养,但自己的自身情况并不适合养育孩子,可能还需要年幼的孩子照顾他们,不能上学接受教育,这样的情况下,孩子由谁看管?
因此国家应当尽量使孩子进入一个适合他生活的家庭。要完成这个过程,我们需要专业的评估人员。在我们国家,这个环节是缺失的,不仅缺乏专业人员,也缺乏政策上的规范。
记者:法律认定的孤儿是父母双亡,然而现在社会中还有一部分孩子是父母双方有一方仍存在,但长期消失,没有对孩子承担养育责任;或服刑人员的子女,这些孩子由谁看管?
童小军:这些孩子即事实孤儿。养育他们的责任应该由政府承担。但是,按现有的规定,官办福利机构仅接受父母双亡的孩子,上面所说的孩子是无法进入到福利机构中的,这些孩子就成为无人看管的孩子了。
这些无人看管的孩子即是困境儿童,也就是说,他们的原生家庭还存在,但是已经无法履行监护这个孩子的义务了,孩子已经部分或者全部失去了能够支持他健康成长的家庭环境。这个时候,政府的责任就是为这些孩子提供替代家庭的照顾。然而在这一方面,政府目前还没有承担其应承担的责任。
政府应理清与民间机构关系
记者: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机构介入了,却把自己推进了尴尬的处境。
童小军:目前,这种尴尬是必然的。政府承担养育孤儿的责任,并不意味着社会不能参与。尤其是那些无法进入到官办福利机构的事实孤儿,民间机构通过自筹资金,组织人力,为处于困境的儿童提供养育服务。但是,民间机构参与孤儿养育,必须是在政府的监管之下进行。由于这样的机制不存在,才出现了袁厉害事件。
记者:在袁厉害事件之前,政府默许民间收养机构存在,但出事后,政府的态度从默许转为遣散,你如何看待这种转变?
童小军:我认为政府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孤儿的养育是政府的责任,才会出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行为。
如果遣散民间机构,将孩子重新放入福利院中,政府同样需要考虑:现有官办机构有没有能力接收现有民间机构养育的孩子,如空间够不够、生活照顾人手够不够、医疗康复专业人员够不够等等。如果没有周全的考虑,这些孩子的养育还是会出现问题。
记者:政府应当如何做,才能承担起孤儿的养育责任?
童小军:首先政府应当认清自己的职责,理清与民间机构的关系,了解怎么做对孩子是最好的。
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应当尽快出台法律法规,明确政府责任,规范养育这些孩子的程序及标准,支持并监督专业的人员或机构落实这样的程序。
本报记者侯雪竹李晋
上一页123
• 中国角型毛巾架行业运营态势与投资潜力研究报告(2018-2023)
• 中国直接挡轴市场深度研究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2021-2023)
• 2018-2023年KTV专用触摸屏市场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
• 中国回流式高细度粉碎机市场深度调研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3)
• 2018-2023年中国原色瓦楞纸行业市场深度研究及发展策略预测报告
• 中国雪白深效精华液市场深度调研及战略研究报告(2018-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