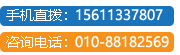
编者按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其中一个突出的、重要的、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对于社会特殊人群的管理。
在法律领域中,特殊人群主要指吸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社区矫正对象、精神病患者、艾滋病人、问题青少年、留守儿童及服刑劳教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等等。而特殊人群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则特指某些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及其生存状况。
目前,在社会心理上,对特殊人群仍存在歧视和不信任现象。特殊人群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大多数人并不知晓。而这种沟通上的障碍,既不利于社会公众客观看待、宽容接纳特殊人群,也不利于特殊人群回归社会。为此,《法制日报》视点版特别推出“特殊人群生存状况系列调查",希望通过对特殊人群中典型人物生活的呈现,唤起全社会对他们的温暖和关爱。
□特殊人群生存状况系列调查
一场大雨将湖北省武汉市“洗”了个透。
小区物业公司保安队队长杜胜跨过一个小水洼,走到一名妇女面前说:“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能在小区里面卖菜。你就在小区门口,一样有生意,大家进进出出买菜也方便。”站在杜胜面前的中年妇女,脚边是一个菜篮子。听了杜胜的话,她笑而不语。这是记者近日在武汉市长丰路一个保障房小区内看到的一幕。
“她们也不容易,但是小区有管理规定。”杜胜转头对《法制日报》记者说,“走,我再带你们看看这个小区。”
杜胜很在乎这个小区,也很在乎他的这份工作。相较于曾经的吸毒经历,现在的生活“很充实,也很开心”。
今年50岁的杜胜,与毒品“亲密接触”18年。他的讲述,将记者“带进”了一个吸毒人员的真实生活。
“大款”堕成瘾君子
“大款”这个称谓,属于上世纪90年代初成功“下海”的一群人。杜胜曾是一名实打实的“大款”。
“一辆宝马、一辆丰田,这样的家当在现在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在1994年是很难得的。”杜胜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上世纪90年代初,杜胜辞去了国营大厂的工作,干起了糖酒副食买卖。“你们单位在北京哪个区?我对北京很熟,去了不知道多少次。有一年我们去天津开一个罐头营销会,开完会,我就带着3个销售员去北京玩了3天。”和记者说起曾经的辉煌,杜胜咂着嘴不停地摇头。
杜胜家楼上住着一名民航飞行员,曾对他开玩笑说:“你在天上的时间比我在天上的时间还长。”
“这话一点儿都不夸张。当时为了谈生意,经常坐飞机。”面对记者,杜胜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起一件事,“有一次,我在广州订制了一条裤子,因为生意忙就提前回武汉。后来裤子做好了,我还是坐飞机去拿回来的。”
“生意做得大,朋友也多,有些朋友当时就在吸毒。”杜胜说,“当时没多少人知道毒品,生意圈里,吸毒是一种时髦,是一件很‘玩味’的事。”
“最初,我对吸毒这种事很厌恶。因为那些朋友三天两头就找我借钱。”当时,杜胜还规劝这些朋友,“没有钱就不要吸了。”朋友告诉他,说不吸就不吸?没有这么简单。
听到这样的答复,杜胜有些不服气,“我就不信了,哪有这么邪”,“我就是这样开始接触毒品的”。
接触毒品一段时间后,杜胜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不适的症状,“有些上瘾”。心知不好,杜胜跑到岳母家住了一个星期,希望能克制自己。但是,事与愿违。从岳母家回来后,杜胜彻底被毒品俘虏了。
“最初我还只是口吸毒品。”杜胜告诉记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吸毒人员里,80%的人都是口吸毒品,只有20%的人是注射吸毒,“而且都是三五个人一起,在宾馆开一个房间”。
一次吸毒,杜胜从朋友那里知道了注射这种方法,试了一次之后,他觉得“一针下去,嘴巴、鼻子里都是香味儿,头皮一炸,很舒服”。一次“绝妙”的享受后,杜胜开始了白天黑夜颠倒的生活。
杜胜将吸毒生活形容为“三慌一倒”:慌货、慌钱、慌位子,吸毒之后倒在床上或地上。这样的生活让杜胜把所有的积蓄、家里值钱的东西都“给”了毒品。没钱买毒品了,就找朋友借,朋友甩下2000元钱,留下一句话,“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钱越来越少,朋友越来越少,杜胜开始琢磨偷东西卖钱买毒品。那是一个夏日的中午,杜胜坐在自家小区的院子里,想着如何弄钱,看到了不远处的双杠。“那是生铁做的,值钱”。杜胜走出小区,叫来一辆货车,把双杠运出去卖了800元钱,给了货车司机150元,剩下的都买了毒品。
“吸毒这么多年,认识了很多吸毒的人,他们吸毒的原因各种各样。”杜胜说,有的人是因为好奇,有的是听说吸毒可以治牙疼、胃疼。“其实,沾上毒品的往往都是意志坚定的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能够坚持不上瘾,相信自己的克制力”。
“吸毒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就是社会影响。”进入21世纪后,杜胜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吸毒,而且多是在一些娱乐场所接触到毒品。“一进那些地方,门口就会有人问你要不要试一下,年轻人好奇,一试就不能自拔”。
“这些很常见的卖毒品的方式,为什么却很少有人查?”一番述说之后,杜胜向记者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吸毒人员多“三无”
“有时候想,吸毒真的是件很没意思的事情,也经常下决心去戒毒。但只要一有钱,就还是想到了毒品。”吸毒18年,杜胜两次劳教戒毒、4次强制隔离戒毒,这些还不包括他参加的自愿戒毒。
1997年,杜胜第一次被劳教戒毒。解教的那一天,他的母亲到劳教所接他。杜胜找母亲要了几百元钱,说是买几件体面的衣服重新开始生活,转头却是“还愿”去了——吸毒人员解教后,都会有一个心理,戒毒这么长时间,再吸一次就不碰了。
几乎每次戒毒之后,杜胜都在重复上演一些场景——“还愿”;在家老老实实待上几天;出门溜达,但原来的朋友避之唯恐不及,无奈之下,只有找曾经的“毒友”,复吸。
“空虚,没有朋友。”杜胜说,几乎每个吸毒人员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戒毒的信念稍有动摇,就将前功尽弃。
杜胜的说法,在记者随后的采访中得到了印证。
“吸毒时间较长的人员几乎都处于‘三无’状态:无家庭、无朋友、无工作。”武汉市柏泉强制隔离戒毒所副所长吴光金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家人的离弃、社会的拒绝,让吸毒人员看不到希望。
相对来说,杜胜是幸运的,他的家人没有放弃他。2009年4月,杜胜被送往武汉市柏泉强制隔离戒毒所。这一次,他将近8旬的母亲已没有气力再去强戒所了。“千万不能再吸了,我没有时间去看你了,再说你也要为儿子着想。”母亲的话让杜胜汗颜。
进所时,已无颜见亲人的杜胜在登记时,说自己是孤身一人。但没过多久的一次接见日上,民警通知杜胜说有人来看他,这让杜胜有点惊讶。
“儿子带着女朋友来看我,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杜胜告诉记者,儿子的女朋友对他说,“叔叔,您要好好照顾自己”。当时,他都不敢抬头。
家人的关心让杜胜坚定了戒毒的信念。在柏泉强制隔离戒毒所,他参加了同伴教育互助团队。
何为同伴教育互助团队?记者在对武汉市劳教局副调研员朱明慧的采访中得到了答案。
朱明慧说,成立戒毒人员同伴互助团队,就是为戒毒人员提供科学、系统、规范的教育平台,引导戒毒人员“远离毒品、挑战自我、重获新生”。以团体辅导、主题讲座、专题训练等形式,营造积极的学习气氛,增强戒毒人员相互关怀与支持的意识,提高戒毒人员戒除毒瘾的信心,解决生活中产生的心理困扰,达到自助与助人的目的。
“参加互助团队,是有甄选条件的。”杜胜说,“第一就是戒毒愿望强烈才能申请加入;第二必须是入所4个月之后方可加入。到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戒毒人员都是在公安机关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经过3个月的生理脱毒后才入所的。入所后的前4个月,主要进行队列训练等行为养成训练。其后进入心理脱毒治疗。”
“在互助团队的学习,我知道了什么是‘高危环境’,什么是‘过敏原’。”杜胜说,“曾经的那些毒友对我来说就是‘高危环境’,他们的行为属于‘过敏原’,经常接触会影响到我。”
杜胜至今仍记得一次团队学习中的游戏:两根新旧铁轨,旧铁轨上有一个孩子在玩耍;新铁轨上竖着一个“严禁玩耍”的警示牌,但是有3个孩子在铁轨上。“我就是火车司机,要选择的是从哪条铁轨上通过。”杜胜说,当时很难选择,不管从哪根铁轨上走都是残酷的。“我最后选择了从新铁轨上通过,因为这是不遵守规则的代价”。
就杜胜所说的心理游戏,记者专门采访了柏泉强制隔离戒毒所心理咨询师李红军。李红军告诉记者,每名戒毒学员的文化水平不同、个人能力有差异,但是通过这种心理游戏,他们都会有不同的认知。
这样的学习加上家人的良苦用心,让杜胜在离开柏泉强制隔离戒毒所时,向民警熊建国保证:“我再也不吸毒了”。
2010年11月19日,杜胜离开强制隔离戒毒所。当时,他身上揣着700多元钱。不过,这次他没有去“还愿”,而是和一起解教的学员来到戒毒所外的一个小餐馆,点了一盘牛肉,要了一瓶酒。
社会合力很重要
按照武汉市的政策,解教的吸毒人员可以申请低保。回家后,杜胜找到了居委会申请办理低保,但是回应他的却是爱搭不理和白眼。
感觉受到歧视的杜胜拨通了民警熊建国的电话,他想不通。
“你别多想了,明天回来喝酒,咱俩聊聊。”熊建国的态度让杜胜心里舒服了很多。
杜胜回归社会后的遭遇,柏泉强戒所的民警其实已有准备。
“在所内教育时,学会求助是一个重要课程。因为很多学员回归社会后,一旦遇到挫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毒品。所以,我们希望戒毒学员知道如何宣泄压力,面对挫折。”李红军说。
2010年年底,在朋友的介绍下,杜胜参加一个物业公司的保安应聘。身体好、能说会道,也有处理各种事情的经验,杜胜很顺利地应聘到了保安这一职位。“当时,公司并不知道我曾经是吸毒人员”。
曾经从商的阅历加上豪爽的性格,杜胜在调解物业纠纷方面很有一套,业主和公司也对他多有信任。工作不久,杜胜就成为管理二十多名保安的班长。其间,他每个月到当地派出所进行尿检,一直保持着戒毒操守率。
2011年10月,杜胜被物业公司负责人叫去谈话。负责人说,公司负责的另一个小区刚启用,物业纠纷比较多,也比较乱,希望他能过去负责,担任保安队长。
杜胜扛着行李到了现在工作的保障房小区,却发现,小区不大,也没什么问题,并不像公司领导所说。
摸不着头脑的杜胜打听一番后得知,原来有人告诉物业公司负责人,说他曾是吸毒人员。
“虽然我没有当面问公司领导,但调我过来,肯定是因为这个。”杜胜说,“这也不能怪别人,我现在也没什么想不通的地方,就觉得现在事情太少,没什么激情。”
就杜胜的遭遇,《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戒毒工作不是戒毒场所一家能完成的。当戒毒学员离开强制隔离戒毒所后,需要其他相关部门做好衔接工作。”吴光金感叹道。
而朱明慧的看法是,目前社会在接受解教戒毒学员的问题上还有欠缺,“一方面,个别单位对吸毒人员存在歧视;另一方面,有的社区还缺乏足够的人力和专业的心理辅导人员,无法对回归社会的戒毒人员进行心理疏导”。
“武汉市有个‘心桥之家’,每周三下午由心理专家、志愿者和民警与已经回归社会的戒毒人员沟通,听他们讲一周所遇到的烦心事,帮他们排解压力。同时,也向他们传授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另外一个方面,通过这种活动,让这些学员互助巩固戒毒成果。”朱明慧说。
每周三下午,杜胜都会雷打不动去参加“心桥之家”。“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自己要认真去做。”杜胜说。(余飞 胡新桥)
• 中国角型毛巾架行业运营态势与投资潜力研究报告(2018-2023)
• 中国直接挡轴市场深度研究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2021-2023)
• 2018-2023年KTV专用触摸屏市场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
• 中国回流式高细度粉碎机市场深度调研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3)
• 2018-2023年中国原色瓦楞纸行业市场深度研究及发展策略预测报告
• 中国雪白深效精华液市场深度调研及战略研究报告(2018-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