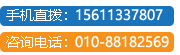
随着食品安全问题凸显,一方面是越来越多城市近郊农夫涌现,一方面更多的消费者也试图建立自供渠道,各种形式的社区支持农业开始在中国大城市兴起。
在农药、化肥、抗生素被广泛滥用的今天,消费者和生产者终于开始相互支持和相互拯救。
图一:有机农夫市集最核心的理念就是让消费者和农户直接建立联系。
继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之后,上海农好有机农夫市集也在上周开集了。
随着食品安全问题凸显,一方面是越来越多“城市近郊农夫”涌现,一方面更多的消费者也试图建立“自供”渠道,各种形式的“社区支持农业”开始在中国大城市兴起。生产者团体和消费者团体都正在试图建立自己的规则,而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消费者社区的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不同于传统地理划分,他们变成有相同理念的网友群体。
在农药、化肥、抗生素被广泛滥用的今天,消费者和生产者终于开始相互支持和相互拯救。
台湾主妇的“绿色实践”
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社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1987年,当时一群家庭主妇意识到不能再坐视社会经济变迁下的环境破坏,决定从自己做起,改善环境质量并提升生活素质。经过20多年的发展,至2009年底,社员已超过3万人,股金总额超过1.1亿元新台币。
为消费社提供货品的是一些有机农场及农民。消费社并非采用一般的有机认证系统,而是由产品部的工作人员实际花时间去接触、了解,寻找与消费社理念相吻合的人,有时甚至需要花上2年时间。
而消费社除了给社员们提供蔬果、肉、蛋、奶与水产等绿色食品,还开办育婴、托儿、托老、养老、丧葬等服务业务,而且不只停留在共同购买的层面,还通过各种活动,促使社员主妇爱护环境,实践绿色生活。
主妇联盟
如果“妈妈团”对农场主道德感产生怀疑,合作便告吹
刘宇璟现在是一个四岁孩子的母亲,怀孕时她开始特别关注国内的食品安全问题,她在超市购买有机蔬菜,之后还自己找了一小块地,种了两年菜。2010年7月,她和社区附近几个年轻母亲开始寻找北京郊区种植“更健康”蔬菜的农场,把找到的菜用车从农场运到小区。“刚开始,完全是为了孩子,后来我逐渐发现,妈妈团可以变成事业”,她说,最初,“我们自己搭上汽油和时间,后来越来越多的妈妈们加入了我们”。
在北京回龙观,“妈妈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发展到有上百个稳定购菜的会员。她们在一个网络社区召集、分享自己寻找到的健康农产品。共同购买的力量显而易见,这一百多个稳定的健康农业消费者开始吸引北京郊区对健康农业感兴趣的农场主,一些农场开始主动联系“妈妈团”希望提供健康农产品。
刘宇璟说,“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进一步甄别”。她们会先和农场主聊一些简单的技术问题,比如长了虫子怎么办,怎么给土地施肥,还包括一些细节的问题。如果农场主不能自圆其说,或者在谈话中令妈妈们对其道德感产生了怀疑,合作便会告吹。
由于在施肥、管理虫害等方面需要更多的人工和技术,定位为“健康农产品”的售价高出普通农产品一倍多。而判断农场主是否值得信任,变成了决定消费者行为的关键。有时候,消费者会相信有信仰的人,“一根筋”的人;有时候,农场主的特殊经历也会吸引潜在的健康农业消费者,比如上海崇明岛的贾瑞明,他不喜欢城市的约束,从白领变成了返乡务农的农民,租了上百亩地,亲自下地干活,而且只种水稻。“对人的感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为了监督,我们会随时和农场主保持联系,有时候会预约过去看,有时候是不期而至。”刘宇璟说。
刘宇璟是全职太太,她本人有寻找健康食品的需要,也有时间去寻找最合适的供应商,这些因素对于“妈妈团”的形成和快速发展都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网络消费社区
费用通过淘宝交纳,争论在豆瓣上进行
“这些妈妈们很厉害,”常天乐说,“她们是中国新兴中产的代表,她们开着车去找菜,她们知道的农场比我们还多。”
常天乐供职于一家名叫美国农业与贸易研究所的NGO组织,在其中担任研究员工作。2008年,这个机构赞助了一个中国女孩子到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家社区支持农业的农场里务农,这个女博士叫石嫣,她在美国做了半年真正的农民后,回国后创办了北京市郊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如今已经是中国最成熟的社区支持农业农庄之一。
像北京“妈妈团”这样的消费者群体,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虚拟的网络社区。而在美国、欧洲已相对成熟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CSA),在中国一些大城市也有过实践经历,如成都河流研究会2005年启动了保护府南河上游计划,就是通过组织安龙村的农户生态种植,再把他们种植的菜卖到城市社区。
小毛驴的石嫣在美国实习学的也是社区支持农业。她去的农庄规模不大,除了农场主夫妻,就只有她做实习,三个人干活。农场的100亩土地,就有20亩种菜,他们一共拥有33个会员,这种小规模的定向供应一共持续了13年。石嫣说,这对美国夫妇也不想扩大自己的生意,他们更希望和购买者保持比较紧密的关系,享受生活,同时相互支持。
这33个会员不是生活在共同的小区,而是一群有共同生活理念的人,这种模式在美国非常常见。在石嫣实习的明尼苏达农场附近,有另一个农场主朋友,配送给250个会员,也是一个虚拟社区。
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社区的概念在逐渐发生变化,美国社区支持农业的经营者会把“社区”定义为在一个州之内,通过在BBS等网络社区聚集“同类”。
在上海,通过网络形成购买者的社区,也已经渐成雏形。通过“豆瓣”网络社区的联络,上海健康消费采购团(简称“上海菜团”)在成立半年后,逐渐发展到了40多个会员。和北京“妈妈团”一样,上海菜团成员仍然主要以年轻母亲为主,她们最关心的是健康的厨房食材。
这完全是一个通过网络组织的社区。购买行为以及会费、活动组织费用的交纳,都是通过新开设的淘宝店进行交易。社员的讨论则在豆瓣小组上进行,上两个月,他们激烈地讨论了社团未来的发展方向。所有会员和外来者,都可以在网上看到这个消费者社区正在关注的议题,包括意见不一致时产生的观点冲撞。为菜团奉献了更多时间和精力的志愿者,是否该获得一定形式的报酬?诸如此类的问题争论,完全公开透明地在网络上展示。
有机认证要不要?
上海菜团选择了“小农”而非大型有机农场
上海菜团的发起人易晓武,做过多年志愿者。这个团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核心的五位理事,会每周开一次电话会议,他们既是消费者,也是社区工作的志愿者,支撑这个虚拟社区的运转。“我们主要希望支持志愿生产健康食品的小农”,易晓武说,他希望寻找的小农,农场主应该一半以上时间下地耕作,而且承诺不使用农药化肥。按照这个标准,菜团在崇明岛上寻找到了两个供应商,一个是种大米的贾瑞明,还有一家梦田生态农庄,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回归农业的城市青年。而且,由于他们算是小农,和菜团的力量可以对等。
寻找合适的农场通常并不容易。比如菜团考察过的一个规模较大的农场,他们从外面购入有机肥,“可能会增加农场不可控制的环节”。上海已经有一些形成规模的有机农庄,比如多利农场、百欧欢农场,这种大型农场也未纳入菜团的考虑范围。
菜团所寻找的食品,并非机构认证的有机食品,而是基于对种植农户个人的信任而购买的健康食品。追随这个消费者机构的会员,会每隔一段时间有亲近农场的活动。这同时也是一种监督,易晓武说,但购买依然主要基于信任。
不使用农药化肥并不容易,对那些刚进入这个行业的生产者来说更是如此,农业技术显得非常重要。有时候农场主要说清楚自己采用的替代品,比如有机肥的来源,通过什么方式防治病虫害,是否使用生物制剂来代替农药。比如小毛驴农庄,它们的有机肥料来源包括从外购买的蚯蚓肥和自己农庄的堆肥。
通过有机认证和通过消费者认可,对农场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现在中国共有20多家有机标准的认证机构,可以按照生产商的市场需求,按照中国、欧盟、加拿大等国的有机标准对食品进行认证,但认证的高门槛———包括对土壤和水源的处理、每年交纳会费等,无疑会把相当多的小农户都排除在外。
周泽江是国际有机农业联盟(IFOAM)在亚洲区的代表,这个机构提出了有机的四个原则:“健康、生态、公平、关爱”,不仅要求农产品健康,还要求对环境友好,同时兼顾对农民的社会公平。周泽江指出,人们追求健康食品时,不必局限于“有机认证”一种方式。现在中国一些农场主用自然农法、生态农法,也可以令食品生产更加安全,同时对环境更友好。如果没有通过有机认证,可以不用有机标签,只要能向消费者说清楚自己的种植方式。
并非有机才能卖出更高的价钱。周泽江在美国耶鲁大学附近的农夫市集,曾经看到过三种农场主同时练摊,一种是经过美国农业部有机标准认证的农庄;另一种是“农民的承诺”(farmer‘spledge),有几十亩土地的农民联合成立一个小组,组内相互监督,这种摊位上会出现农民的承诺书,声明按照健康方式种植;还有一个只有几亩地的小农场,由耶鲁大学师生经营,就叫做耶鲁农场。消费者是否选购农场产品,完全取决于农场声誉,耶鲁农场的农产品售价和有机认证食品价格就不相上下。
小毛驴农园模式
“社会参与认证”,敢于接纳没有利益关系的人
目前,经过有机认证的农场,仍然是有机行业内的主流。要符合有机条件的生产,需要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如上海浦东市郊的多利有机农场,就对外宣布自己花了两三年时间来做土壤转换。
北京市郊的小毛驴农园则选择走不认证的道路。这个农园位于北京西六环,得到了海淀区政府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支持。
“如果走常规渠道,比如进入超市,我们可能需要认证。但我们没有参与认证的打算,我们考虑通过这个农场,建立一种可以在农户间推广的模式”,创办者石嫣说,认证一年要交两万块钱,这也是普通农户无力承担的。
对比机构认证,石嫣介绍说,小毛驴走的是“社会参与认证”的路子。这种参与包括:市民认养土地,组织消费者到农庄活动,以及招募实习生。
小毛驴农园有一个区域是专门做认领劳动份额,它们被切割成平均30平米左右的耕地。市民可以在这里种植蔬菜,农场提供技术指导。虽然这个农庄距离市区很远,还是有退休老头老太隔天坐一两个小时的公交车过来,在地里种菜。新的实习生也会不断来到这个农场。
敢于长期接纳他人,意味着农场具有透明度,在社会式参与监督中,不断有外来者参与很重要。在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泽江看来,敢于接纳没有利益关系的人,特别是招募实习生,让不拿工资的农学生到农场耕读,都是农场接受外界监督,并和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的方式,因为实习生来来去去,“如果农场的生产方式有什么问题,这些年轻人肯定会说出去”。
而消费者在农作物种植中的参与,也成为农场经营者和购买者交流的方式。袁清华是小毛驴农园的农业技术指导,某天上午,一个人穿着西装来到菜园,他就教“西装”怎么翻地。因为下午还要上班,“西装”就在脚上包了一层塑料纸下地干活。这个穿着西装耕地的场景在袁清华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通过钱,可以在超市购买任何东西,人们就不会珍惜自己的所得”,袁说,他们必须看到从种到收的过程,才有可能对土地和食物产生感情。
市集的红娘角色
如果农民与买菜人成为朋友,大量使用农药可能会有压力
“社区支持农业现在是大家对食品安全无能为力情况下的一种自救行为,不光是社区居民支持农业,而是互相支持。”常天乐说,如果大家都不做,没有人会走出第一步。
今年以来,北京、上海相继出现面向市民的有机农夫市集。常天乐是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组织者,这个市集已经在北京举办过几次,北京市郊从事生态农业生产的农庄陆续在这个市集上与消费者见面。虽然借用了“有机”概念,但这个市场上出售的并不是经过认证的有机产品。
市集最核心的理念,就是消费者和农户直接建立联系。如果农民认识买菜人,彼此很熟悉或者逐渐变成朋友,在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的时候,可能会更有道德压力。常天乐说,而消费者也可以借助和农户沟通的机会自己选择。
在北京市集之后,上海市集也在上个周末开了初集,市集上出售的仍然以小农户没有经过认证的健康食品为主。这个市集的组织者蒋亦凡提出一个“中间市场”的概念。他说,“我们要让消费者知道这中间还有不同级别的健康食品,而且一分价格一分货。”这样新进入行业的人可以用优质的产品换得优价,而不会被有机标准阻吓而干脆选择不进入农业。
这两个市集都定位为公益,而且作为新鲜事物都吸引了公众关注。参与市集的人也会提供建议,比如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有人对比国外的市集,会说你们的产品不够丰富,有的人会说,这个市集太像一个菜市场,没有什么教育功能,还有的消费者会提出意见,说其中的一些摊位令他们产生了怀疑。“确实有一两个摊位有这种情况,他们也不是我们最初邀请的,而是自己过来,我们不好意思拒绝”,常天乐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接下来就要和农场主沟通”。
消费者提出越来越多问题,令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组织者认为,有必要设置一些规则。常天乐写了个征求意见稿,提出对参与农夫的要求,除了要求生产者认同有机理念,还要求他们公开透明,愿意和消费者沟通生产方式和方法,其中包括种子、肥料、饲料来源,防病防虫的方法,动物的生活空间和密度,是否使用大棚等信息。
这些信息对于消费者来说非常重要,他们可以依据这个沟通过程,判断农户是否值得信任。而作为市集的组织者,只是依据行业声誉和考察,提供见面机会,剩下的全部要消费者自己完成。
上海农夫市集的组织者蒋亦凡则在免责声明利益说明,本身不对产品质量进行任何担保。已经有很多人问如果农户售卖不健康蔬菜怎么办,他的回答是,“消费者不应等待权威来替他们把关,而应在市集中成为主角,自己去判断这些瓜果蔬菜是否健康”。
市集的组织者更愿意把自己也看成消费者。北京农夫市集的组织者就经常在微博上讲,他又在哪里买了什么东西。常天乐说,“最起码,进入市集的人是我们信得过的,我们没有把不相信的人放进来,而且我们也在这里购买”。
消费者联盟“在路上”
北京“妈妈团”逐渐走往商业之路,上海菜团更多考虑公益方向
除了价格高昂的有机农业,更多农民参与、外延更广阔的健康农业也逐渐变得可能。“关键是我们自己行业内部要做好规范,”上海生耕农社的李冰博士在一个行业交流的现场说,“如果没有有机认证,我们如何说明自己?”
在生产者联盟正在制定规则的同时,中国的消费者联盟也在寻找一种可持续运作的方式。在媒体的关注中,常用台湾主妇联盟、日本守护大地协会和中国的消费者联盟作对比,它们出现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背景同样是消费者和NGO组织不满农药化肥的滥用。据《小康》杂志报道,日本的守护大地协会已发展成为拥有2500个生产会员、91000个消费会员,年营业额达153.2613亿日元的庞大组织。
可以对比的是,随着消费者力量团体的增加,这些成熟的消费者团体,其角色也从简单的消费者转变为出资者、经营者。消费者联盟可以强大到追溯食品生产的每个源头。而在中国,消费者联盟还处在发展初期,北京“妈妈团”的组织者刘宇璟就很不习惯把自己和台湾主妇联盟作比较,她说:“没有什么可比性,我们就处于人家30多年前的发展水平”。
在通往强大消费者合作社的路上,中国的消费者社团还有很多需要摸索的地方,比如,是选择商业模式,还是更偏向公益路线。最初,这些消费者社区的形成是受到组织者自身消费需要的推动,但在人数逐渐增加之后,最初几个核心的组织者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劳动。他们的团体也面临发展方向的选择。
北京“妈妈团”的刘宇璟开始逐渐往商业的方向发展,她并不讳言这一点。由于有一百多个会员,工作量急剧增加,除了自己全职之外,“妈妈团”还雇佣了一个工作人员,同时租用了一个门面。这些费用都需要通过一定比例收益来分摊。
而上海菜团,在两个月前也在公开的网络平台上激烈地讨论过这个问题。菜团的核心会员都有自己的工作,以志愿者的方式参与,是否应该建立激励机制?菜团的理事徐曦提出,应该给参与召集的小组长一些报酬,这种报酬可能只简单到一袋米。
易晓武则在更多地考虑菜团的公益方向,比如参与组织上周末的上海农夫市集。“如果以后我们足够强大了,或许可以考虑直接介入农场生产”,他说,“但现在我们还在路上”。
• 中国角型毛巾架行业运营态势与投资潜力研究报告(2018-2023)
• 中国直接挡轴市场深度研究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2021-2023)
• 2018-2023年KTV专用触摸屏市场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
• 中国回流式高细度粉碎机市场深度调研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3)
• 2018-2023年中国原色瓦楞纸行业市场深度研究及发展策略预测报告
• 中国雪白深效精华液市场深度调研及战略研究报告(2018-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