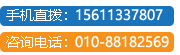

2012年2月25日,科学家、散文家陈之藩在香港逝世。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发文表示,将一直记得文学家陈之藩教的道理,“一个民主社会可贵之处,在于提供一个可以让勤苦自立、努力向上的人民实现梦想的公平环境”。马英九说,在念中学的年代,陈之藩的作品尚未进入中学教材,但已广受喜爱,不论是《旅美小简》、《在春风里》,还是《剑河倒影》,都是脍炙人口的畅销书,也因此都是你我世代的共同记忆。陈之藩的著作不只激荡了文学想象与美学感受,更让大家一窥科学与人文互动的火花,这是一般文学作家不易展现的特色。陈之藩的作品,不受时空限制,“将持续感动我们,启发我们”。
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说,陈之藩的去世,是中国人和华人的损失。金耀基指出陈之藩是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发展的主要人物,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同时高度赞扬陈之藩在散文方面的成就:“我阅读过他的散文,他是最近几十年来最好的散文家之一。”
诗人余光中评论,陈之藩是“当代一流的散文家”。他的散文不是要追求散文的艺术,而是用散文来表达思想,“比较像思想家”。
作家龙应台发文悼念,陈之藩的散文是他们好几代人的共同人文记忆,可以说,他和朱自清、徐志摩一样,代代相传,并称“陈之藩就在我们不灭的温馨记忆里”。
与胡适的朋友圈交往
陈之藩先生一生,总在写信。有时写给朋友,有时写给读者,有时写给自己。余光中的《尺素寸心》中说:“陈之藩年轻时,和胡适、沈从文等现代作家书信往还,名家手迹收藏甚富,梁(实秋)先生戏称他为man of letters,到了今天,该轮他的自己的书信被人收藏了吧。”
1947年,陈之藩在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读书,有一天在广播里听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眼前文化的动向》的演讲,觉得与他的意见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遂给他写了一信。胡适很快回信,彼此的通信由此开始,陈之藩回忆:“他的诚恳与和蔼,从每封信我都可以感觉到。所以我很爱给他写信,总是有话可谈。”在陈之藩给胡适的信中,充满了对中国时局的关注,许多见解现在看来是先知先觉。后来陈之藩将1947年前后给胡适的13封信集成《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一书。
1947年夏天,陈之藩应胡适之约,到北平东厂胡同一号拜访。两人只聊了一会,北京大学训导长贺麟来了,要跟胡适商量学生闹学潮的事,陈之藩就告辞了,和胡适实际上没说多少话。对第一次和胡适见面,陈之藩回忆:“我见过的教授多了,胡适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大派。”
1948年6月13日,陈之藩在雷海宗所编的《周论》上发表长文《世纪的苦闷与自我的彷徨—青年眼中的世界与自己》,见地独到,为胡适的朋友圈击赏。陈之藩说:“现在让我写也写不出来。就因为那篇文章,他们都吓坏了。他们是胡适、金岳霖、冯友兰、沈从文。他们彼此讲,问胡先生这人是谁?胡先生说:他常给我写信啊。”
陈之藩也给金岳霖、沈从文写过信。他在北洋大学电机系读到一半时,对国家前途感到悲观,想改读哲学救国,就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这事在陈家掀起了轩然大波。为了改专业的决定,陈之藩到清华大学跟金岳霖见过一面。金岳霖问:“你为什么要入哲学系呢?”陈之藩说:“我悲观而又爱国。”“什么叫悲观呢?”“我不知道。”“悲观就是你认为有一套价值观念以后,比如你觉得金子很值钱,你当然设法要保存,把金子拿到家里来,拿到兜里来,但是保存之无法,金子被人抢走了,乃感悲观。”一席谈之后,陈之藩打消了转学的念头,昏沉地回到北洋大学。后来陈之藩写了《哲学与困惑—六十年代忆及金岳霖》一文。
大概是在东厂胡同看完胡适的第二天,陈之藩便到中老胡同看沈从文。两人谈兴正浓时,沈从文的太太张兆和出来了,拿着一堆小孩衣服。沈从文就作了介绍。陈之藩当时全校2000人,女同学只有三四个,漂亮女人没见过。张兆和的漂亮完全在陈之藩的想象之外,她说:“沈先生对陈先生的文章很欣赏。”陈之藩傻傻地也不会答,连一句敷衍的话也不会说。“沈从文真是好,看到我觉得他太太很美,所以他就给我下台阶,他就把话题引到另外的题目上去,我就镇静下来了,镇静下来以后一会就好了。”
1948年,陈之藩在北洋大学毕业,由学校派到台湾南部高雄的台湾碱业公司工作。那时找工作很难,陈之藩在北平也找不到事做,当他坐船到了台湾以后接到沈从文的信:“天津《益世报》里有份工作,也就是写些文化,跟电机完全不相干。”后来,沈从文写信说:“你千万不要回来,华北到处是血与火。”
唐德刚写胡适的文字“太轻佻”
陈之藩在台湾碱业公司的主要工作是修马达,实在无聊。他在北洋大学的老院长李书田在台北的编译馆主持自然科学组,便叫他过去工作。当时梁实秋主持编译馆的人文科学组,一看陈之藩写的书就说:“我们人文组也没有这样的人,这人怎么跑到自然组了。” 后来梁实秋当了馆长,说要提拔天才,把陈之藩的薪水加了一倍。陈之藩领到工资时并不知情,便去找会计:“你是不是搞错了?怎么这么多,扣了税多了几乎一倍。”会计说:“你们梁馆长批的。你问他呀,你问我干什么。”
胡适第二次回到台湾时,陈之藩去看他。胡适说:“你几时回来的?”陈之藩说:“我从哪儿回来?”胡适:“美国。”因为经济拮据,陈之藩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去美国留学,胡适回美后就寄了一张支票给陈之藩,用作美国要求留学生交的保证金。
陈之藩在考试前,人家告诉他得看《Time》杂志,结果笔试正好就考他预备好的那一段,一个生词也没有。口试时,主考的领事从美国来,刚学中文,客厅里坐着一大堆人,领事从屋里出来,练练自己的中文,一看“陈之藩”,就大声说“陈—吃—饭”,大家都笑了。领事不好意思,说:“我说得不对吗?”陈之藩说:“你说的全不对。”“应该怎么说?”“陈之藩!”领事就跟着说了一遍,口试就这么通过了。
那时陈之藩还没有钱买去美国的单程飞机票,又不好意思向胡适借路费,便延迟了一年赴美,写了一本物理教科书。他又遇见一个贵人—世界书局的老板杨家骆。陈之藩回忆:“杨家骆对我真是好,其实这些人都对我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跟我说你编译馆做事的人,你编的书卖给谁,你得找一个教授联名,把他名字写在前头,把我名字写在后头,这才可能出书,就请一个师范大学的教授挂一个名。可笑这个书稿到杨家骆那儿,请求他考虑出我这本书,他就这么一看,他说好啊,不要师范大学教授挂名,就出我自己单个人的,我头一本书就是他出的。出书我也就拿到去美国的路费,大概5000块台币,美金大概1000块左右,就这么去了。”
1955年,陈之藩赴美国宾夕尼亚大学攻读科学硕士学位。读书期间,陈之藩应《自由中国》编辑聂华苓之约,撰写《旅美小简》,一篇篇从美国寄到台北。他回忆:“到美国以后的生活是这样的:上半天到明朗的课室去上课,下半天到喧嚣的实验室玩机器,晚上在寂静的灯光下读书。常到周末,心情上不自主地要松一口气,遂静静地想半天,写一篇小简,寄回台北去。”(《旅美小简》前记)这本书中,《失根的兰花》、《钓胜于鱼》等名篇后来多收入中学课本。
从陈之藩赴美到1960年胡适回台,正是胡适在纽约最是冷清、最无聊赖的岁月,陈之藩有幸和胡适谈天说地,说短道长。陈之藩回忆:“所谈的天是天南地北,我所受之教常出我意外,零碎复杂得不易收拾。”(《在春风里》序)
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也是写胡适在纽约时期的生活,读来让人感觉胡适挺可怜的。陈之藩却说:“也不像他说的那样,不是丧家之犬。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写的袁世凯很详细,从前很多我不知道,写得很好,写胡适的就太轻佻,形容不出胡适这个人来,形容胡适的词不是很恰当。”
当陈之藩获得美国宾夕尼亚大学科学硕士学位后,应聘到曼城一所教会学校当教授,这时才有能力分期偿还胡适当年的借款。当他还清最后一笔款时,胡适写信说:“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400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1962年,胡适在台北逝世,陈之藩连写了九篇纪念胡适的文章,后集成《在春风里》。胡适的风度和胸襟,陈之藩写得让人想流泪:“生灵涂炭的事,他看不得;蹂躏人权的事,他看不得;贫穷,他看不得;愚昧,他看不得;病苦,他看不得。而他却又不信流血革命,不信急功近利,不信凭空掉下馅饼,不信地上忽现天堂,他只信一点一滴的、一尺一寸的进步与改造,这是他力竭声嘶地提倡科学、提倡民主的根本原因。他心里所想的科学与民主,翻成白话该是假使没有诸葛亮,最好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这也就是民主的最低调子。而他所谓的科学,只是先要少出错,然后再谈立功。”
1962年3月31日,陈之藩给已故的胡适写信:“适之先生,天上好玩吗?希望您在那儿多演讲,多解释解释,让老天爷保佑我们这个可怜的地方,我们这群茫然的孤儿。大家虽然有些过错,甚至罪恶,但心眼儿都还挺好的。大家也决心日行一善,每人先学您一德,希望您能保佑我们。”半个世纪之后,陈之藩和胡适在天堂相会,相信不再寂寞了。
左手研究科学,右手撰写散文
1969年,在美国任大学教授的陈之藩获选到欧洲几个著名大学去访问,于是接洽剑桥大学,可惜该年剑桥大学的唯一名额已选妥。陈之藩不想到别的大学,索性到剑桥大学读博士研究生。
一到剑桥大学,每个人都叫陈之藩为陈教授,并在他的屋子前钉上大牌子,“陈教授”。在那里,陈之藩写下了《剑河倒影》。陈之藩说:“剑桥之所以为剑桥,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干各人的,从无一人过问你的事。找你爱找的朋友,聊你爱聊的天。看看水,看看云,任何事不做无所谓。”
在聊天、演讲、读书之间,陈之藩写出的论文颇有创见,被推荐到学位会,作为哲学博士论文。毕业时,陈之藩想起生平敬重的胡适:“适之先生逝世近十年,1971年的11月,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老童生的泪,流了一个下午。我想:适之先生如仍活着,才81岁啊。我若告诉他,‘硕士念了两年半,博士只念了一年半。’他是会比我自己还高兴的。”(《在春风里》序)
1977年,陈之藩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担任客座科学家,当时他所研究的是“人工智慧”。有一次,他偶然在大学图书馆看到香港中文大学招请电子工程系教授的广告,决定回到东方。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创系主任是“光纤之父”高锟,陈之藩后来也担任了系主任。其间,陈之藩与当时的研究院院长邢慕寰不断讨论博士学位的创立,终于使电子工程系产生了香港中文大学的首位博士。
陈之藩左手研究科学,右手撰写散文。他的专业是电机工程,著有电机工程论文百篇,《系统导论》、《人工智慧语言》专书二册。但他常对朋友说:“我现在不大爱看的,恐怕是几年后电脑在半秒钟即可解决的问题;而我爱看的,是一百年以后电脑依然无法下手的。回溯起来,罗素上千页的《数学原理》的成百定理不是由60年代的电脑五分钟就解决了好多吗?可是罗素的散文,还是清澈如水,在人类迷惑的层林的一角,闪着幽光。”
1984年,陈之藩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课程部讲《科技时代的思想》时指出:“科技既以数量来作衡量,凡是不能用数量来衡量的东西,就难见其功了;科技既以实验来作证明,凡是不能作实验的东西就难以为力了。科学固然提供了可靠的知识与有效的方法;但是,我们把科学所描述的世界与我们感到的真实世界相比较,就知道科学成就之可怜了。与人最接近的是他的心灵,科学似乎并无所知。比如:永恒何所指谓,人人急切地想知道,科学不能答;上帝是否存在,也是人人热衷地想明白,科学却无所助。美与丑的分野,善与恶的分际,科学是避而不谈的。不谈还好,如果勉强去谈,答案是近乎可笑的。”他反思科学与文艺的关系:“用计算机可以把莎士比亚的句法排列与比较,但计算机写不出《哈姆雷特》来;用计算机可以把梵•高的笔法解析,但计算机却画不出《星夜》;用计算机可以模仿贝多芬,但却创作不出《田园》来。”
在科学与人文、民主与专制之间苦苦思索,陈之藩不甘心地提起笔来写散文:“我们当然对不起锦绣的万里河山,也对不起祖宗的千年魂魄;但我总觉得更对不起的是经千锤,历百炼,有金石声的中国文字。”晚年在香港,他写成了《散步》和《思与花开》两本散文集。
陈之藩不仅写散文,还译诗。他翻译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不朽名句: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 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他在《时空之海》中说:“如果说只许用诗来说明爱因斯坦的时空观,也很难找出比布莱克这几句再神似的了。”在文艺复兴时代,科学与人文是紧紧结合的,而种种学科的界限却在日后渐渐形成。在陈之藩描述的爱因斯坦的故事中,也许可以看出爱因斯坦是一个“文艺复兴人”。
在“专才”成群而“通才”寥寥的时代,陈之藩也正是东方的“文艺复兴人”。
• 中国角型毛巾架行业运营态势与投资潜力研究报告(2018-2023)
• 中国直接挡轴市场深度研究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2021-2023)
• 2018-2023年KTV专用触摸屏市场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
• 中国回流式高细度粉碎机市场深度调研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3)
• 2018-2023年中国原色瓦楞纸行业市场深度研究及发展策略预测报告
• 中国雪白深效精华液市场深度调研及战略研究报告(2018-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