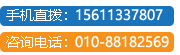
编者按: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改革开放,春风化雨,改变了中国,影响并惠及了世界,这40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浓墨重彩的40年。
面对这个举世瞩目、影响深远的伟大实践,中国网财经联袂今日头条共同邀请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共同记录这个伟大时代。
这一期我们专访了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人工智能与制度研究中心主任许成钢,看看他对改革开放有哪些独到的见解。

许成钢简介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人工智能与制度研究中心主任。2016年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2013年获得孙冶方经济学论文奖。2018年出任罗汉堂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网财经:您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制度?
许成钢:改革开放是非常重大、非常基本的方向性选择。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按照苏联中央计划经济制度模式,建立了全面的中央计划经济。所谓中央计划经济,是中央自上而下的、非常详细、具体、全面的计划。其前提是,中央必须直接控制所有的企业和资产。这是从上到下,控制生产和执行计划的基础。
之后经过大跃进和“文革”,从基本上改变了中央直接控制所有企业的制度,把中央各部门控制几乎所有企业,改变成各级地方政府控制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而且,把每个县级及更高层次的地区,都发展成基本自给自足的经济。这种中国创造的向地方分权的极权制与苏联式的极权制有重要基本变化,这把中央计划改成了以各级地方政府为基础的行政计划。但在所有制以及反对市场经济方面,与苏联经济没有差别。
中国网财经:您认为改革开放带来哪些重大变化?
许成钢:第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了行政计划经济。
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变化,是产权的变化:从1978年完全禁止、完全没有生产资料的私有产权,到现在大部分中国的国民经济产值由私有产权生产。首先,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变化,是允许外资进入,这意味着私有产权的进入。所以,开放本身就意味着产权的重要变化。
改革开放早期的另一个产权变化,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称“包产到户”。这实际是土地使用权的部分私有化。后来经历的乡镇企业发展,民企大发展,国企改制,所有这些积累成为今天看到的产权的变化。
第三个重要变化是在法治方面的变化。我们知道,试图用市场来取代行政计划,试图合法化私有产权,都必须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来支持制度变化。在改革开放开始时,必须首先恢复在“文革”中被破坏了的公检法,同时建立整套跟市场相关、跟私有产权相关的司法制度。这是巨大的挑战。
中国网财经:您如何看待中国当前改革?
许成钢:中国已经经历的改革开放,集中在三个重要方面:市场、产权、法治。这三个方面是密切互补、不可分割的。只有市场的改革但是没有私有产权的发展,那就是苏欧失败的改革;有市场有产权的改革但是没有建立法治,造就的是混乱的市场。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私有产权从无到有的过程。这里讲的私有产权指的是生产资料。私有产权在改革开放开始时,是不被承认的,是不合法的。因为法律禁止私人办企业,所以在改革开放早期,很多企业家被抓到监狱里去。直到1986年,中国才建立了第一部《民法通则》,其中承认法人的私有产权,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企的发展有所帮助。但是,自然人的产权仍然没有得到承认,即自然人的私有产权仍然可以被侵犯,被剥夺。在宪法不保护私有产权时,这个《民法通则》在保护私有产权方面,作用极其有限。
直到2004年修订《宪法》,中国才在宪法里正式承认了私有产权的合法性,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是改革开放中一个里程碑性质的变化。与此配套,直到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中国第一次承认了自然人的产权。这样在司法的具体过程中,无论是法官也好,律师也好,如何解释私有产权就有了明确依据。
中国网财经:中国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是否已基本完备?
许成钢:法律自身的规定必须要正确完备,同时还要得到公正的执行,才算完备。从法律规定的角度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和民法都保护私有产权。许多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几百年的历史。这正是其发达的根源。日本明治维新时,从欧洲学来了相关的这些法律,并且努力执行。清朝在1906-1908年新政时,从日本和欧洲学来以宪法和民法保护私有产权,但执行的困难大很多。
在法治方面,中国最大的问题在执行,在司法制度,这是艰巨的改革。为了保证法律能够得到公正的执行,法庭必须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就是没有人可以干预法庭,干预法官。保证法官、法庭在面对任何人、任何机构的时候,都用相同的法律来判断。如果法庭在司法过程中倾向于控辩双方中的某一方,法庭就丧失了公正的基本立场。当法庭总是丧失基本立场时,无论写在纸上的法律是什么东西,都丧失了作用。
中国网财经:中国经济当前还面临哪些主要问题?
许成钢:改革开放至今,改革国企,改革国有资产的管理,也是改革的最难部分之一。国有资产的一个最重大问题,或者性质,就是所谓的“软预算约束”问题。软预算约束问题指当机构或企业(例如国企和地方政府)资不抵债时,仍然可以借助外部(例如中央政府或国有银行)的救助得以生存。这使资不抵债的机构不面对破产的风险。由此在这类机构或企业中,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
产生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最大根源,是国有资产。因为国有资产资不抵债时,政府会来帮。而私有资产在资不抵债时,不太可能会有政府来帮忙。因此私有企业运作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小心,提防破产。这就是国有资产运作的基本规律,和私有资产不同的基本点。
软预算约束问题对国有资产的致命性,是学术界和政策界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清楚认识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体制的整体崩溃,其背后最基本的一个重大机制就是全面国有制下的软预算问题。因为他们在二十多年的改革中(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不能克服软预算约束这个致命的问题。
和苏欧早期的改革相比,中国改革最大的成绩,就在于民企的大发展,私有产权的大发展。伴随私有资产的硬预算约束性质,当硬预算约束下的资产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大大增加时,抵消了部分国有资产软预算约束问题带来的负面后果。这使得中国避免了苏欧经济当年的失败遭遇。
在改革早期,中国的学界、政策界,以及曾经对中国改革有很大帮助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都曾对软预算约束的危险性有很强的认识。把治理软预算约束,或硬化预算问题,当作头号目标。即便如此,在1990年代末,国有部门的不断恶化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也曾给中国带来很大困难,甚至危险。面对这个重大挑战,当时的中央政府推动了一系列改革,使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得到遏制。【编者注:有数据显示,1996-1998年,国有企业从11.38万家下降至6.5万家,减少幅度达到42%,同时减员增效、下岗分流,1998年至1999年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下降约2200万。】当时国有部门的大量下岗,就是在治理致命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时,不得已进行的痛苦改革。虽然过去的改革在遏制软预算约束问题上取得成效,一度把软预算约束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降低了。但是,由于国有部门比重仍然很大,问题不但没有从基本上解决,而且由于在最近十几年里对这个问题的忽视,软预算问题在过去几年里,以新的形式卷土重来。最突出的就是人所周知的产能过剩和高杠杆率问题。
中国网财经:中国目前杠杆率偏高和地方债问题您如何看待?
许成钢:杠杆率为什么这么高?高在哪里?什么造成的?两个最大因素,一个是地方政府,一个是央企——国企里最大那部分。它们杠杆率最高,为什么最高?因为软预算约束,地方政府和国企高管都不害怕破产,敢于借贷,这就是产生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根源。
根子上的问题不解决,所有其他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这就有点像一个得了癌症的人发烧,你给他用降烧的药,温度下去了一点,他的病没有好。
如果坚持保持国有资产的规模,为了减小国有资产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对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仅有的办法就是努力帮助私有资产更快地发展。用这个办法,减小国有资产在整个国民经济里的比例,稀释了软预算约束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作用。
中国网财经:民营经济要发展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许成钢:民企老板们最迫切需要的是落实宪法和民法的规定,保护他们的产权。与保护产权同等重要的是保护和保证合同的执行。这些都是市场秩序所必须的。此外,民企在融资方面的困难,民企进入许多领域的壁垒,都是需要从体制改革上认真面对的问题。
民企融资困难比国企大很多,原因是,金融领域的企业基本都是国有。垄断金融领域的国有金融机构,在放贷时有倾向性。再加上国企的软预算约束问题,都使得国企融资与民企不同。
中国网财经:现阶段我们能采取什么具体措施?
许成钢:应该创造条件,落实法治,让民营企业能够安全,能够发展。
司法制度改革方面确实面临一些困难。一种可行的办法是,首先针对专业程度较高的司法领域,建立独立于所有地方政府和司法系统的专业法庭。例如,建立直接隶属于最高法管辖的金融法庭。按照这个思路,逐步推开独立的法庭,使得越来越多的领域的执法能够相对独立。
中国网财经:您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是否乐观?
许成钢:从改革的角度来说,改革开始时私有产权是非法的,但现在民营企业家也都登堂入室。当然我们有大量的问题需要去解决,但是和那个时候比已是天壤之别。在民企大发展的推动下,中国从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比印度,比非洲多数国家都穷),变成了中等收入国家。在过去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民企可以有如此大的发展,让我们有理由乐观。
当然乐观的前提是我们要对有待改革的问题有正确的认知,要知道中国目前的问题在哪里,要深刻理解私有产权保护和相关司法制度改革,制度建设的迫切性、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