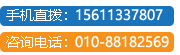

高晓松
“我以前一直以为喝酒能让人自由,最后因为喝酒失去了自由。”去年5月17日,高晓松因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6个月,处罚金4000元人民币。对于高晓松而言,这6个月不是一场审判,而是一次救赎。
事发后的高晓松对警方表示:“我是违法行为,我愿意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随后,他又在询问室亲笔写下“对不起,永不酒驾”,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庭审中,他说“酒令智昏,以我为戒”。面对公诉人对其醉驾的事实和指控罪名,他表示“自愿认罪”,并数次打断律师以证据瑕疵发起的无罪辩护,“律师,我已经认罪了。我相信法律公正。”
有人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高晓松认错诚恳、个人形象加分不少。一个清华才子,校园民谣旗手,恃才傲物的游吟诗人,从书香门第,一路名校,少年成名,走遍世界,到看守所漫长的184天,高晓松的经历充满话题。
乐评人李皖在《两个高晓松》中这样描述当年27岁、发表了个人作品集、开了个人作品音乐会、正处在顶峰的高晓松:“在歌里,高晓松一直在回忆,让人以为他是个内向、伤感、学生气十足的人。现实中的高晓松恰恰相反,他轻佻、贫嘴、痞里痞气,满脸是浮夸的笑,满嘴是七荤八素的杂话,没一秒钟能够安静。”恃才傲物是朋友对高晓松最具负面性的评价。高晓松说,幸好老婆没认识年轻时的自己,“我年轻的时候飞扬跋扈,现在想想,自己都讨厌自己。”
“根红苗正”的高晓松离开大学的第三个月就发财了,当年就有车,有三万块钱的大哥大,大哥大上还吊了一个三千五的BP机,有一个特别贵的呼号,就一个数,呼“6”,那一年他才22岁。“那时候多张扬,一定要让自己特别与众不同。22岁发财了,24岁发表第一首歌《同桌的你》还出名了,你想我那时候有多膨胀。”
接受本报专访时,高晓松梳理了自己“在里面”六个月的生活,还表示决定远离过往的那些张扬、膨胀和不靠谱,“一个从小被惯大的名校生,20多岁的膨胀可以被大家原谅,但这种人在40多岁的时候应该担当更辽阔的使命,做一个名校生应该做的。”
这一切,正如高晓松在歌中所写的: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
出来混,早晚要还的
说句心里话,如果我面临的是无期徒刑,那我可能会辩解,但这个最高就是六个月,男子汉大丈夫就为了六个月变成五个月去上诉,人生缺这一个月吗?
新京报:你曾说,希望出来之后生活可以慢下来、不想一再“被消费”,现在你觉得做到了吗?
高晓松:还好吧。因为你在这个名利场里自己都消费自己,别人当然也消费。我更多的是希望别人消费我的作品。
我比较倾向于以报恩的方式“被消费”,如果你对我非常好,那你消费消费,我也配合配合。比如《大武生》时期的支持,以及其他让我觉得很温暖、不离不弃的人。其实回头看,所有人都对我很好,媒体对我也很好,没有往死里打,包括围着我们家、堵着机场也都不是负面恶意。刚出来一两周有点忙乱,因为我适应不了,但慢慢地我也能控制住节奏。
新京报:大家对你庭审时道歉的态度印象非常深,之前大家对你的印象是游吟诗人,比较自由散漫。
高晓松:我经常后怕,幸亏老天爷在这个时候给我刹住车,追到人家尾上。要真是给人撞伤、撞死了,赔钱是另外一回事,你心灵也受不了啊。你再恃才傲物、再浪子,你也是一个人,而且做艺术的人内心其实很柔软的。道歉肯定是真心的,因为我太后怕。老天对你好,你不能认为自己没做错。再加上我是特别信“出来混,早晚要还的”,我那几天的感觉就是终于要还了。那就一起都还了吧。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要还的是什么呢?有人觉得六个月判到顶有点重了。
高晓松:有很多人跟我说量刑过重,我说,我以前也干过好多不要脸的事呢,不要脸虽然不能判刑,但你自己心里知道你干过很多不要脸的事。我觉得就该判重点,把以前欠的全部的债这次一起还了。
新京报:判之前你紧张吗?
高晓松:不太紧张。我已经听到一些消息说会重判,律师说可以跟法官谈判,因为血液化验单上三个签字的人都没有检验师执照,我说,你不用去弄那些事了,他有没有执照我也喝醉了,我觉得自己对自己惩罚或者叫“救赎”都是应该的。
说句心里话,如果我面临的是无期徒刑,那我可能会辩解,会听从律师的,咱们能减多少是多少,因为那是一辈子的事。但这个最高就是六个月,男子汉大丈夫就为了六个月变成五个月去上诉,人生缺这一个月吗?不就一片树叶子从树上落下来了嘛,有点太小气了。而且最后真是在里面六个月我计划的读书写作都没弄完。
我后来跟所长开玩笑说,要是再住几天交多少钱?所长说,反正国家给你们一人一天16块,纯属国家补贴,你还是别花纳税人的钱了,你出去吧。
用神奇感削弱绝望感
六米高的房顶上有一盏昏白的灯,左边躺着一个小偷,右面挤着一个黑社会,觉得好神奇啊,我挤在这样两个人之间睡觉。
新京报:进去前想过将要面对的具体生活吗?
高晓松:我当时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能不能安静思考。反正来什么面对什么呗,即使里面是“躲猫猫”“洗冷水澡”,那也看看你是不是一个男子汉。后来我进去里面有几个大哥跟我说,晓松,在外面牛逼的人,在里边也一样牛逼,在外边是个怂人,在里边也是一个怂人,你不用担心。我说我本来也不担心,我都40多岁了,我还会怕在一个地方变成特别傻的、天天被人欺负的人吗?而且我还有一点点说不出来的小涌动:让我来看看,这世界的另一面是什么样子,有些什么人。
新京报:第一天晚上睡着了吗?有绝望感吗?
高晓松:睡着了,因为从洛杉矶飞回来、参加完《大武生》发布会就去交通队,已经36小时没睡觉了。但第二天没睡着,躺在那儿,看着六米高的房顶上有一盏昏白的灯,左边躺着一个小偷,右面挤着一个黑社会,觉得好神奇啊,我挤在这样两个人之间睡觉。
刚进去也睡不到好的位子,大家都论资排辈,谁呆的时间久谁就慢慢蹭到门边上去。这个呼噜响,那个有口臭,你躺在那儿,你不停地说这神奇,这神奇,因为你要觉得神奇,就会削弱绝望感。慢慢就好了。
新京报:最初的不适感和“神奇感”过去之后,后面是否会有大量无所事事的时候?你更习惯于发呆还是思考?
高晓松:我是一个非常不爱主动思考的人,艺术这东西没法思考,艺术是一种很直接的感受。在里边经常发呆,尤其下雨的时候,看不见,只能听远处的雨声,我让自己凝神,就仿佛站在辽阔的、自由的雨中。
我曾经有一个月都没跟同屋人说过两句话,把人都问完了,干吗的、什么背景、犯了什么罪、他怎么生活的,到第四个月,我已经没兴趣问了。
来回来去就是这么几种人:偷摩托车的中学生、卖发票的、行贿的大款、受贿的官员。以前你觉得社会好多角落你不了解,了解一通后发现也就那几个角落,没多少神奇的人。后来我就开始翻译。
拿个塑料瓶子扎个洞,每天晚上看《新闻联播》时装满水,电视上有时间就开始漏,漏到《新闻联播》完正好漏到一个位置,用黑色涂一下,就知道这是半小时。
新京报:你在里面写东西,有笔吗?
高晓松:每个人都是一样,一床被子、一床褥子,没有枕头,没有被单、床单,因为那些都能杀人。把褥子卷一点到头上就当枕头睡了。里头没有任何插口,怕你触电。能自杀和能伤害别人的东西都没有。笔也是只有最柔软的笔芯,刚开始特别别扭,后来我自制了一支笔,把早上喝的粥涂在纸上,卷在笔芯外头,卷成一支比较粗的笔。
马尔克斯的《昔年种柳》原本没人出版也没人翻译过,谈版权时我就跟马大师和他的经纪人说,一个热爱他的犯人,在监狱里用柔软的笔芯在极其昏暗的灯光下,也没有桌子,只有一个板,他坐在板上,抱着两床被子,边翻译边写,希望他能给予出版的许可。
新京报:在里面会觉得时间很漫长吧?
高晓松:里头没有钟,我们自制了一个钟。老祖宗教的东西还挺好,就是沙漏。用水做沙漏。拿个塑料瓶子扎个洞,看《新闻联播》时装满水,电视上有时间就开始漏,漏到《新闻联播》完正好漏到一个位置,用黑色涂一下,就知道这是半小时,加长一倍就是一个小时。我们有一个人专门负责看表,几点了,他就坐在那个塑料瓶旁边说现在几点。
新京报:这些是你带进去的创意还是本来就有?
高晓松:都有。里面人的智慧无穷,再艰苦,总得生活下去,鲁宾孙在无人岛都能生活。我还有一个钱包,是老犯人走的时候留给我的,用包装袋做的,非常精巧,但里面没有钱。我半年后再见到人民币和美元,觉得比我想的面积大很多。
想到女儿,六个月很长很长
在里面,大家聊到女儿时都会热泪盈眶。所有人都想自己老婆。因为只有老婆不离不弃,最终只有老婆记得给你送件衣服,只有老婆定期来看你。
新京报:家属去探望你时,你是什么感受?
高晓松:家属每个月可以去探望,我老婆、我妈都来。我老婆第一次哭得要死,我妈原本极为乐观和豁达——我妈从小教给我们很多,其中有两句网上还挺流行的:“人生不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妈自己走遍世界,我从来没见她为我哭过,结果她抓着那个探视的铁栏杆还哭出来几滴眼泪。我当时跟我妈开玩笑说,看来我真是亲生的。
新京报:你哭了吗?
高晓松:我妈、我老婆来看我时我都没哭,我还特高兴,安慰她们。我女儿来,她没哭,我倒哭了。因为她特别高兴,她们跟她说,我拍戏呢。我女儿说,爸爸你什么时候拍完戏呀?我说很快了,其实一想还有很久。想到漫长的人生,觉得六个月不长,但一想到女儿,六个月很长很长。一想到女儿,你觉得两个礼拜都很长。我大概就哭了那么一次。
在里面,大家聊到女儿的时候都会热泪盈眶。首先,聊到老婆会热泪盈眶。富商、干部、黑社会大哥、赌场老板、组织卖淫的,所有人都想自己老婆,这点让我挺感动。因为只有老婆不离不弃,最终只有老婆记得给你送件衣服,只有老婆定期来看你。我也特想我老婆。年轻人没什么可想,年轻人在里边自得其乐。
想起他们,心里很难过
我说,出来后你给我做助理吧,他特别高兴。我出来后跟经纪人、家里人商量,所有人都坚决反对,你怎么能找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做助理?
新京报:我看过的监狱题材电影里,知识分子在狱中多少都会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你觉得这种身份在里面给你带来的差异、需要调适的东西,难吗?
高晓松:对我来说不难。我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知识分子,还有一个身份是北京孩子——北京孩子从小学痞子,上街打架,我中学大学都因为打架挨过处分、严重警告,所以对我来说没什么大问题。
有一点世界观的问题,但我也没办法,这不是监狱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我跟小孩讲,你出去别偷了,可以干点正经事。但年轻人完全不接受你的思想,年轻人坚定地认为我唯一的罪行就是没钱,我有钱就没有罪。里边的年轻人基本清一色是这么想的。每个人都说,我出去当然偷啊,那我能干什么?我只要偷多点,我有钱了我就没有罪,你看有钱人被抓进来了吗?都是我们被抓进来。所以我没办法说服他。有的时候会觉得挺难过。
新京报:你在里面会给这些年轻人教一些什么吗?
高晓松:我开始还教两个孩子写诗呢,我把十三韵给他们默写一遍,让他们每句的结尾都押着韵。有一阵子我们屋还掀起了一股人人写小诗的小高潮。做学术的知识分子比较封闭,做艺术的人虽然是知识分子,但愿意接触更多的人。如果真是学术型的知识分子,在里面可能会比较难过。
新京报:里面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人吗?
高晓松:有一次我没哭,但有点热泪盈眶。是送我大哥,他判了七年,要下监狱了。他这手夹着被子、褥子,那手提着一个塑料盆子,50多岁的人了,有点驼背,很绝望地离开了。把他送到门口,我们俩热烈拥抱,我说,我出来之后,一定会坚持去看你一直到你出来。
我很少交到这样一个天天跟我睡一起、给我讲很多事情的人。他很了解看守所里所有的人际关系,给我仔细讲了每个管教、每个科长的脾气、性格,教给我怎么适应,对待杀人犯也别怕,怎么对付他们。我现在每次吃点好东西或者特别自由想干嘛就干嘛的时候,就想起这个大哥。大哥还在里面煎熬着。
我还看上了一个年轻人,长得特别端正,人品也很端正,虽然是孤儿,但是从不乞求,非常正派的一个孩子。他犯的罪挺倒霉的。他做服务员,客人喝醉了揍他,被揍得实在受不了,还两下手,把人家眼眶打裂了,算防卫过当吧。他特别老实、勤恳、能干活,我说,出来后你给我做助理吧,他特别高兴,一直怀着希望。
这事儿还让我心里很难过,我出来后跟经纪人、家里人商量,所有人都坚决反对,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还是有歧视,你怎么能找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做助理?他前两天出来了,我给了他一笔钱,还给他报了新东方厨师学校,希望他能努力在人海里不要沉没。
有时候会挺怀念里边的生活,大家都以特别简单的方式在一起,清贫、清淡的日子,管教也很单纯。我应该这么说:即使中国社会有一些坏的习气,但看守所还是最清水衙门的地方。说句最不好听的话,到了看守所都是非穷即傻,也没什么油水。
从倒数一百天开始数日子
最后一天我很波动,后来别太刻意了说我要怎么怎么样,到处去赎罪,也没必要,就顺其自然地生活。
新京报:出来前一个礼拜会为今后的日子规划一下吗?
高晓松:我从倒数一百天开始数日子,我想别太早数日子,数日子有点难过。我特别痛恨七月跟八月,这两个月都是31天。数到还有一个礼拜就不数了,因为要数就得数小时了,我就赶快把没看完的书,没写完的东西赶完,那个状态已经有点像在外边的时候要被逼着交稿了,赶快写东西。
新京报:最后一天情绪波动了吗?
高晓松:到了还有一天的时候可能我有点哆嗦,因为我这半年还好,不算很长,里边三四年羁押的人到提前一个礼拜要出去的时候都睡不着觉,然后经常问我外边现在什么样,我出去能适应吗?在里面,牙刷这么短套在大拇指上,因为它也是凶器。勺子也这么短,是软的。我后来回到家拿一个这么大的牙刷刷牙都不会了,这太大了,怎么刷啊。最后一天我很波动,我想了很多,我想出来以后我怎么生活,我本身又不是一个爱想事的人。后来我说就自然去做吧,别太刻意了说我要怎么怎么样,到处去赎罪,也没必要,就顺其自然地生活。
表现优越感是一件讨厌的事
有几件事我是下了决心的,首先是不做生意,只卖艺。再有,以前那些傻逼的事,到了40多岁也应该改了。
新京报:如果说到这六个月的反省或者收获,你觉得是什么?
高晓松:有几件事我是下了决心的,首先是更加坚定了不做生意,不成立公司,不会成立一个电影公司、音乐公司,坚定了只卖艺。因为人生已经过了一半,能够有创造力的时间也就剩十几年,我已经入行18年,我猜最多再有18年,60岁就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了,所以60岁会去教书,这是我早就算计好的,教书、翻译书、读书。坚持只做作品,只做艺术家。再有就是对钱看淡了很多——我本来就看得很淡。我大概是我认识的人里面这岁数唯一没买房子的。买点衣服,给老婆买买包,吃吃饭,能花什么钱?这两件事都对,我出来之后更加坚定这个想法。
再有我对自己说,以前所有那些傻逼的事,即使不坐牢到了40多岁也应该改了。有些时候觉得以前怎么就那么二呢,明明是一个三十岁的人,老拿十八九的心态来造,让人看了觉得这人特不和谐,这人怎么书也没少读,但老疯疯癫癫的。
出来以后我对自己说一定要低调,一切低调。到现在出来一个多月我觉得还行,不难做到。包括写写微博,跟大家在一起做事情都三思而后行,我觉得挺好的。当然也不会低调到违背我性格,那倒没必要,最后不是O型血、天蝎座的北京孩子了。
新京报:大家对你比较普遍的评价就是恃才傲物,优越感比较强,你觉得这次经历会改变你的这个特点吗?
高晓松:优越感是一个没办法的事,现在还会有,就是不表现出来了。优越感不是坏事,坏的是你老在别人面前表现这个优越感,那就是一个挺讨厌的事。我投胎就投成这样了,首先是一个北京人,书香门第,读的全是最好的学校,根红苗正。人家说自己也是四中的,我们都得问问你初中高中都是吗?清华你还得是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建筑系四个最好的系。
我一直生活在领先的阶层。我22岁发财了,24岁发表第一首歌《同桌的你》还出名了,你想我那时候有多膨胀。我在里面回想从前的事,经常把脸捂在褥子里说,我以前怎么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也活该还债。我之前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老婆全家信佛,我跟她说,你可不许求佛任何事,因为老天对我们已经太好了,给你美貌容颜,给我根红苗正,咱该满足了。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生活可能搞错了,这次我小小地把自己的六个月还给生活,总比还别的好。
少说多做,不愿意卖这个事
所有跟我之前签了合同的,不管是音乐、电影、出版都不离不弃。我也没有涨一分钱价。
新京报:因为这次你做了一次非常好的危机公关,形象很好,有传言说你出来之后身价大增?
高晓松:我年轻时那个样子很多人都不喜欢,但是我一旦好一点大家都很接受,我有难了大家都努力地伸把手。所有跟我之前签了合同的,不管是音乐、电影、出版都不离不弃。我也投桃报李,没有涨一分钱价。包括我即将出版的《如丧》这本书,因为合约是在我出事之前签的,本来就没包括看守所中的部分,我一出来就有出版商找我,说给我多少钱让我把里面的东西写出来,我完全可以另出一本,但我还是把看守所这一部分送给原来签约的出版商。
新京报:设想过出来以后,外面的人对你的看法会跟以前不一样吗?
高晓松:会吧,但是我不是很担心。因为会慢慢过去,就是看你怎么做事。所以我当时说我出来少说多做,到现在你是第一个大家看到的专访。首先,因为你太执著,我还挺感动的。第二,《新京报》我觉得是个值得信任的好报纸。第三个,好多朋友也跟我讲适当的时候我可以说说这事,我不愿意卖这个事,因为我是卖艺的,不是卖身的,但对这个社会有点意义的话还是可以说,那我就说这一次挺好。
生活还是对我很好,包括在最关键的时候给我悬崖勒马,免于陷入疯狂。而且正好在整个文化行业大井喷之前,让我能安静下来想一想,以免被裹胁在大潮里彻底迷失了。
O型血都会像我这样,我也没有超越O型血的乐观特质。你(指记者)要是真的去了也没问题。我就见到一两个精神崩溃的,大部分人都能坚持。我还不冤,还有冤的呢,那都咬牙坚持下来了,而且最后也能随遇而安。人生都是写好的剧本,你总能接着走下去。
文艺问答
在里面,文盲也会喟叹自由
里面的每个人都说,愿意付出全部身家包括性命,去换回自由。原来我觉得自由是属于知识分子的一个词,在里面,文盲也会喟叹自由。
新京报:狱中体验给你的创作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未来你的创作会以什么方式进行?
高晓松:我觉得创作方式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我二十年来就这样写东西。但心境会极大不同,回想起许多在外面从未想起的人和事,一缕阳光下最淡的往事。我那时常想起李叔同和苏曼殊(均为民国著名僧人)临终说的两句话:“悲欣交集”和“一切皆有情”。你在看不见天空的地方想外面的世界,觉得每个过往的人和事都有情,都是悲欢,都是缘分,都成了远方。你把心肠拿出来慢慢洗,不着急,慢慢的,就看见了。
新京报:当重新回到平常生活中,对那些被生活的监狱困住的人,你会说什么?
高晓松:我无话可说,这两个世界没有共通的语言。但我会经常发呆,我发呆时,就在想他们。不是怜悯,而是流放归来的人对远方的牵挂。
新京报:在自由被禁锢的时候,你如何看待自由?在生活变规律的时候,你如何看待散漫?在必须手写的时候,你如何看待机器?在看不见月光的时候,你又如何想象和描绘月光?
高晓松:里面的每个人都说,愿意付出全部身家包括性命,去换回自由。原来我觉得自由是属于知识分子的一个词,在里面,文盲也会喟叹自由。其他的,规律还是散漫,手写还是机器,在自由面前都不值一提。至于月光,其实即使你看得见月光,你描绘的也是心中的月亮。
新京报:除了《如丧》和《昔年种柳》两部即将出版的作品之外,你在电影、音乐上的新一年工作计划可以透露一些吗?
高晓松:会开自己的作品音乐会,我猜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还是有很多人愿意静下一个晚上,听听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音乐还会做,电影还会拍,但是会珍惜,做些让自己能热泪盈眶的东西。
最长的那184个日夜
1.干净
因为大家也没事干,整天就是擦,把茅坑擦得能当脸盆使。
进去呆了六个月,首先让我能呆下去的就是里面特别干净。因为大家也没事干,整天就是擦,把茅坑擦得能当脸盆使。大家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十几个人就那么一个茅坑,大家连撒尿都蹲着,特干净。那个茅坑还裂了几个缝,通常裂了缝在自己家里都会有点尿碱什么的,但是这儿没有。大家就这么点儿生活空间,把每个地方都弄得特别干净。然后里面的医生每天两次巡诊,我发现不会病死在里面,剩下的事都能解决。比如能看什么书,书还挺多,都是捐的,那里面有《大英百科》还封着塑料皮从来没人看过,我就开始看。
我开始就想好了我要先干一些什么事,我先干一些不触动心灵的事,因为那时候人都很脆弱,我怕我看小说可能就柔肠寸断,或者我要写作可能就会陷入绝望,所以我就既不看小说也不写作,我就看百科全书,那不会触动心灵。然后我翻译马尔克斯的书,翻译书比你自己创作要好很多,因为你触及的是人家的心灵,而且人家那么老的人的心灵,90岁的绝望,比我绝望多了,所以我就还好。翻译很动脑筋,大部分不靠心灵,而且用脑子想这句话怎么写成中文,马尔克思还特别爱用大段落的大从句,整个一段就一句话全是从句,一个大从句要翻译半天,动很多脑子在这上头觉得挺好。
2.聊天
有一个人我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我出来想要不把他拍成电影?
再有你有想了解别人的欲望,因为你平时没机会跟这些人聊天,现在跟人睡在一个炕上,光着屁股一起洗澡,上厕所大家互相看着,因为茅坑就在眼前。三天以后你跟这些人太熟了,就跟他们聊呗,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有一个人我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我出来想要不把他拍成电影?算了,可能审查通不过。一辈子他的世界只有一个北京火车站,从小就在北京站,做盲流、要饭、偷东西,抢劫等等。高兴的时候他会说,等我出去了我在火车站什么地儿请你吃饭,生气了他会说,你等我回火车站,我找火车站的小新疆弄死你。我问他怎么花钱,因为他偷很多钱,一个月十几二十万,我说你为什么不拿来做点儿生意,做点儿正经事。他说我不会啊,我就会这样。我说那把钱攒起来,他说我攒不住。我说在一个火车站里怎么花钱啊。他说我去网吧里打游戏,在游戏里他很正义,打各种妖魔鬼怪,他买虚拟游戏装备,七万块钱买把刀,两千块钱买个戒指,他每个月买十几万的装备在虚拟的自己身上。他的爱情就是北京站的小发廊,一个火车站就是他全部的人生。
他极其有意思的地方是他跟别人反着,别人受不了闹,他受不了安静,因为多年在火车站,只要一安静他就受不了,他浑身躁动,别人都睡觉了他弄一盆凉水往人脸上洒,把人弄醒,然后被惩罚,但他觉得有意思,他宁可天天被大家折腾,也不愿意安静。所以看到这个人你会觉得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会在一开始把你的多愁善感、自怨自艾那个情绪分散很多。
3.友谊
屋里的大哥对我特别好……他那珍贵的一小盒酱豆腐全都被我吃了。
再有一个分散注意力的就是别人都比你判得重,我们屋里除了有一个醉驾的比我轻,其他的都是重刑事犯罪,还有杀人的,重伤害的,行贿受贿的,组织卖淫的,反正十年以上的有不少,人家都以努力、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未来要判多少年。
屋里的大哥对我特别好,他最后判了七年,他都努力乐观,我有什么可绝望的、不想活的,我才六个月,而且我知道是哪天出去,他最后拿到判决书——七年,那一天晚上是睡不着的,躺在床上想这七年怎么过去。他有一点儿酱豆腐,有一天我特别厚脸皮的跟他说,我想吃一点酱豆腐,他就给了我一块。我们早上只有馒头跟粥,中午是两个馒头一个清水煮白菜,晚上是两个馒头另一个清水煮白菜或者是清水煮茄子、土豆,反正就这三样东西。所以酱豆腐夹在馒头里简直就是无上的美味,他那珍贵的一小盒酱豆腐全都被我吃了。
然后他跟我讲,他说我今年56岁,我认为60岁以后再出来男人这一生就完了,他希望60岁以前能出来,所以要减一半刑。怎么减呢?现有的合法的最快的减刑方法就是陪死刑犯,判决的死刑犯手脚都用手脚铐连着,怕他自杀或者是疯了。你要给他擦屁股,夏天给他擦身子,而且你要舒缓他的焦虑,你要跟他交朋友,直到他被枪毙。这对陪同的人来说心灵伤害是很大的,当然减刑最快,陪一天死刑犯减一天。56岁的老头陪一个19岁的抢劫杀人犯,睡觉还得半睁着眼睛,因为出现过死刑犯夜里精神崩溃抠别人的眼珠子。这个大哥给了我很多鼓励。
据我观察绝大多数人进来十天半个月就会缓过来,精神崩溃的很少很少,有几样东西让我在里面对“人”这件事特别有信心,我看到人的坚强,大部分人都能挺住,确实有很多人我也觉得挺倒霉的。我屋里还有一个电影迷,他居然连我没公映的《那时花开》都看过,他在一个学校医务室工作,工资很低,他跑到MOMA去买原版的电影书,五千多块钱,进口的,没钱就偷了五千块钱的书被抓进来,估计也得判个半年一年。他也很坚强,他出来医生这条路肯定就没有了,但在里面他还会跟我讲讲电影。
4.“自由”
人人都想出去走两步,哪怕去倒垃圾,擦个地,去小卖部扛扛东西,大家都争着去。
再到两个月以后就可以写东西,看小说了。所以就开始自由了,每天给自己安排得很好,因为看守所是不劳动的。我有两个东西要澄清,很多人在网上问我为什么不剃头。强迫剃头的所谓“侵犯犯人尊严”,这种早已经在中国看守所被废止了。我在里边剪了三次头,我实在不想剃光头,三次都是犯了协助卖淫罪的发廊小弟蹲在地下用一个推子给我推短一点,推得还不错。推完了以后我一看跟外边好几百块钱剪的也差不多。
再一个澄清就是我不劳动,看守所是不劳动,劳动是监狱。看守所如果能有活让你干,那是你的幸运,因为人人都想出去走两步,哪怕去倒垃圾,擦个地,去小卖部扛扛东西,大家都争着去。不是我不劳动,在看守所没有要求劳动,偶尔极少数一点活儿大家都争先恐后,是用来奖励那个刑期最长的犯人,在这里已经羁押了三年了,跟大家都很熟,那你就出去扫扫地,扛扛东西,这就已经很幸福,因为谁愿意在那么小一个地方坐着?铁门上只有一个很小的窟窿,心情是很压抑的。头两个礼拜我都不敢看那个窟窿,一看到铁门上的窟窿你就觉得特别绝望,特别想把那个铁门吃了。因为只有那么一个地方,每天下午两点会伸进一个塑料管子,给你开水。
5.生活
大家特别温柔地喂这只猫,因为那是唯一让你感觉到你在生活的一件事。
后来有那么几个月来了一只猫,每天晚上会到这个窟窿来,我们每天留两个馒头喂它。我说这只猫肯定是菩萨,你想想它干吗上这儿要饭,这儿有什么吃的,这儿会有鱼吗?会有老鼠吗?只有馒头。但是这只猫每天都来,大家特别温柔地喂这只猫,因为那是唯一让你感觉到你在生活的一件事。包括隔壁屋里关着头上被砍了七八斧凶神恶煞一样的人,经常听到他在隔壁屋里怒吼其他人,但是这只猫从我们这儿跑到他那屋,他也是很温柔地喂那只猫。
然后再慢慢地你会生活下去,那就是你生活的地方,而不是以前想的说我在这儿咬着牙服刑。那就是你的生活,只不过你不能出来。有一个小小的放风场,也没有阳光,大概十几平米,大家围成一圈在里头走走步。慢慢你就觉得这就是你的生活,那你就这么生活吧。就跟你小的时候一个月半斤肉,二两油,你也就那么生活。在里边一个星期一个鸡蛋,有鸡蛋的那天特别高兴,人很容易适应的,而不是在没鸡蛋的那六天特别郁闷。隔个四五个星期如果你这屋一直都没打架,就能评一次文明监所,奖励是五天的晚饭是有肉的,而且有很多肉,第一天是烙饼卷肉,第二天是粉条炖肉,第三天是蒸的肉龙,第四天是木樨肉,你到那天就特别高兴。那个肉极大地激励大家不许打架,谁也不许打架,一打架就没了。
六个月其实挺漫长的,时间一长你就慢慢习惯了,那就这样生活吧。
(口述:高晓松)
• 中国角型毛巾架行业运营态势与投资潜力研究报告(2018-2023)
• 中国直接挡轴市场深度研究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2021-2023)
• 2018-2023年KTV专用触摸屏市场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
• 中国回流式高细度粉碎机市场深度调研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3)
• 2018-2023年中国原色瓦楞纸行业市场深度研究及发展策略预测报告
• 中国雪白深效精华液市场深度调研及战略研究报告(2018-2023)